母亲喜欢腌制一些食物,我记忆中家里总有一些陶罐、坛子来腌制一些东西。 腌制往往是从白露开始的。八月,新蒜下来了,蒜儿还裹着薄薄的白衣,嫩的,甚至那层薄衣都是嫩的。剥开来,是一头白得似雪的蒜,因为嫩,所以滑。父亲母亲在天井里剥蒜,三角梅放肆地飞舞着,我和堂弟打闹着,时光总是温馨动人的。 母亲先把它们泡在一个搪瓷盆里,那搪瓷盆是白色的,有近乎透明的质感——多年后碎掉了。不过,我记得那白蒜在里面,一粒粒地浮着,生动而别致,有岁月静好的安宁。 泡了一夜的蒜在第二天要被放在盐水中——用开水把粗盐沏了,然后晾凉,把泡了一夜的蒜放在里面。母亲说,蒜辣味太浓,特别是新蒜,犹如莽撞少年,得收收心才好,这样的收心,等于把放肆与张狂全收了进去。三天之后蒜就能吃了,我往往等不到三天。新腌制的蒜有种清香与刺激,辣,但辣得那样坦荡,绝不是老蒜那种江湖的辣。它仍然是白的,白到透明。因为新,因为腌制的时间太短,来不及变黄变红,它仍然带着年轻时的辣和冲动,刺激着我们的味蕾。 直到霜降前后,新蒜总是不停地被腌制。这段时间,家里总有新蒜的味道。母亲新蒸的馒头,就几粒新腌制的蒜,开胃极了。那时候,我和堂弟总是说饿,还没有到开饭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冬天的时候蒜就腌制老了,黄了红了,没了新蒜的清香,也不辣了,多了一种烟尘味道,它油滑了,没新蒜那颗朝气蓬勃的心了。一切过去了,就只剩下这颗老江湖一样的心。寂寞地呆在陶罐中,被人吃掉,或者继续老去。 夏秋两季,母亲腌制的东西最多。因为那时腌制东西最便宜,豆角、萝卜、刀豆、茄子、黄瓜,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拿来腌制。特别是黄瓜,到了旺季便宜到近乎白送。母亲洗净它们,一根根切成黄瓜条,用开水烫了,然后加上酱油、料酒、花椒水,腌制上一陶罐,冬天时佐以稀饭馒头,亦可当作零食来吃。 腌制的过程是漫长的,生动的黄瓜或茄子被腌制成小小的一条,皱了,老了。从前的饱满被杀得体无完肤,到最后失去挣扎,老实地变软变皱,吸了盐水,只是咸,不再新鲜,完全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不在乎。 我们犹如这些腌制的食物,只不过,腌制它们的是盐水,是花椒、食盐、姜片、料酒,而腌制我们的是时间。我们一天天被时间腌制着,曾经的饱满少年如此生动,敢于放狂,绝不谦逊,豪情万丈,敢爱敢恨,但我们的付出,时光都会懂,如果它许不了你一个“梦想成真”,那么它一定会补你一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只不过是或早或晚,或显性或隐性,或物质或精神,不同呈现方式的差别而已。梦想也许会像成年人那样喜怒不形于色、高深莫测,但时光一定会像个孩子,单纯得像一面镜子,你付出就会让你有所获。 又到秋天,母亲忙着腌制新蒜,打电话过来要我回家去取。我想起父母在天井里剥新蒜,那一粒粒新蒜,在母亲手里又生动又新鲜。母亲忙着腌制它们,而时间忙着腌制我们。 我打开摊在手里的书,看到那句喜欢的话:“人生其实很短,最喜欢的,其实也就是年轻的时候那段光阴吧!”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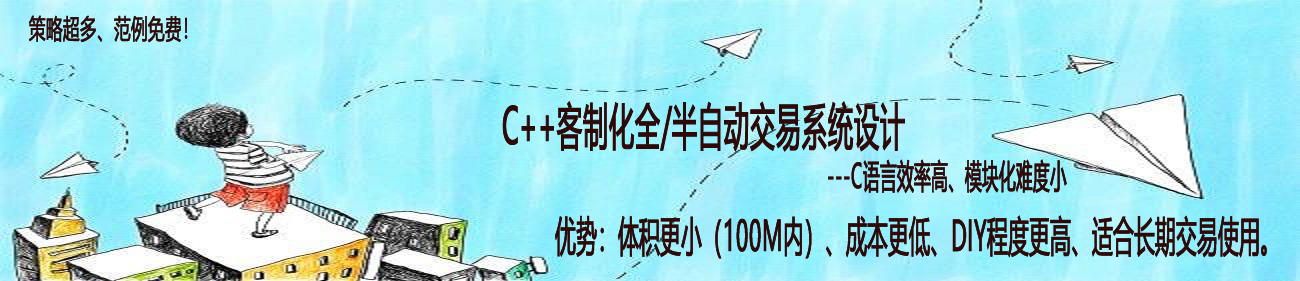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