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摩尔定律”到宏观研究中高频数据大量被使用,科技的手和有形的手共同驱动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但是背后不变的是大类资产的波动率再次回到了历史的静默区间,反馈着宏观经济更深刻的背景——市场缺乏驱动、经济增长点缺失,5月初的市场再次发出了在这宁静之下的暗流信号。
A“摩尔定律”:背后更多是市场的无奈
随着通信技术不断升级,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以及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驱动市场周期的转变。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指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量每隔18至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随着通信效率的上升,以及信息的可得性/透明度增加,市场的反馈周期也有所加快。 但是这种传输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未来经济效率的实质性改善,驱动经济新一轮扩张的步伐似乎已经停滞。资料显示,“摩尔定律”过去是每5年增长10倍,每10年增长100倍,而如今,“摩尔定律”每年只能增长几个百分点,“摩尔定律”似乎已经失效。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维度发生变化,经济体面临的技术转移压力进一步增加。


图为“摩尔定律”逐渐失效 宏观研究中高频数据的大量使用背后蕴含着经济学更深刻的内涵——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精细化。凯恩斯经济学提出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可以通过财政货币的有形之手,来对冲经济的下行,从而达到熨平周期的目的。美国次贷危机后传统货币政策的无效性迫使美联储推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而这一政策的退出过程中,预期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格林斯潘的“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你们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到伯南克和耶伦时代更倾向于同市场沟通,货币政策和市场沟通的及时性上升。 而中国人民银行自2016年开始通过工作日连续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精准调节市场流动性,并自2017年开始通过增加“解释”的方式对市场预期进行更直接的管理。宏观经济周期在央行的逆周期调节之下实现了“熨平”的效果。 周期的“手术刀”在填平短期波动的同时,增加了长期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金融市场在接收到政策“熨平”预期之后的相向而行,带来市场暂时稳定下的交易“拥挤”。截至2019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波动率跌至历史低点,而权益市场和商品市场波动率仍维持在历史低位,这样的市场状态对于监管层而言意味着短期风险的收敛,但是短期稳定性和长期不稳定风险之间依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资金流动本质让当前的政策走向了“熨平”的稳定性选项。


图为风险资产的波动率 B硬币的A面:目前所处的宏观周期 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增长可以简单分解为趋势加周期,当前中美宏观经济周期虽有分化——中国处于底部向上开启状态、美国处在增长顶部回落状态,但是我们理解的趋势向下特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中国经济周期处在筑底阶段 回顾本轮经济周期的走势,可以发现经历了2014—2015年大宗商品冲击下的主动去库存,2016年的市场在美国经济周期继续向上、国内房地产需求刺激叠加供给端去产能影响中,周期开启了往上的转折。实体盈利的大幅改善在2017年年中达到了顶峰,驱动了逆周期政策的边际降低——配合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利率走廊”转向了边际收紧状态。 展望本轮经济的周期,依然在朝改善的方向运行。在2018年经济下行风险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在年中开启了边际上的放松。央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总基调虽然不变,但是多轮的定向降准和监管新规的推迟对于金融市场带来宽松的流动性预期。从周期轮动的角度出发,市场经历了“信用收缩实体稳定+货币政策宽松”的悲观下行,到“信用企稳实体悲观+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乐观反弹,目前市场正处于“信用扩张实体低位+货币政策不再宽松”的再次调整过程。意味着在资产的定价方程中,分母端的估值修复过程已经完成,市场当前处在分母修复(货币到信用的传导)到分子扩张(盈利预期增加带动生产投资活动上升)的转换过程中。在这一转换阶段,分母端的过早退出和分子端的改善不达预期对于资产价格而言都将带来调整的压力。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波动正是信用周期改善向经济周期改善轮动的必经之路,对于中期资产配置而言形成“黄金坑”。 美国经济周期处在筑顶阶段 和中国周期不同的是,2018年财政“逆周期”刺激中拉长的美国经济周期依然处在顶部阶段。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的进行,尽管目前来看市场下调了未来美联储加息的节奏预期,但是实际货币政策仍未转折意味着美国经济仍处在上行的尾部区间。美债2s10s期限利差显示,截至今年5月初利差结构依然在低位运行,意味着本轮周期的尾部延续。我们注意到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数字的改善背后,更多是以出口和库存堆积形式贡献,企业投资依然呈现谨慎的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去年四季度美股调整带来私人部门财富的收缩和消费的谨慎,带来库存消费比的快速走高。 美国未来将继续面临类似2018年的市场冲击或更大风暴。我们将美国短端利率前置大约24个月以反映金融市场货币价格变动对于实体企业盈利和信用状况的影响,美联储2015年年底开始的加息进程对于2018年开始的市场影响正在逐渐得到反馈,2018—2019年的市场虽然有企业回购行为的扩张支撑风险资产,但是随着经济周期临近尾声,其支撑力度预计将逐渐走向衰竭。顶部的延续时间可能很长,却并不改变所处位置状态的现实。 全球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型经济体反馈了本轮经济周期下行的预期。我们看到了中美周期的分化现实,如果是封闭的市场,这样的判断并无错,但对于当前全球化的开放经济体而言,不仅中美之间,而且全球产业链构筑的所有经济体之间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大小经济体之间的走势能印证这一点——大经济体由于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一定意义上可以对冲短期的需求冲击,但是小经济体对于外部冲击的反应就显得更迅速和直接,历史上“荷兰病”冲击的国家不胜枚举,本轮周期中像资源出口型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制造业出口型国家韩国、德国等,近期受到的市场关注尤为明显。在经济周期的下行期,过去传统优势的资源国、制造国将首先承接消费国需求放缓下的负面冲击,然后才是全球再分配规则重构下的重建过程,规则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增加。 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和逆周期要素正在衰竭的路上。要素理论告诉我们,赶超型经济体可以通过分享第一梯队经济体的技术外溢红利而获得增长效率的提升,却在技术封锁的背景下面临效率外溢的缺失;但是如果像技术、人口、资本等增长要素反转以往的趋势,则逆周期政策带来趋势延缓的同时却消耗着逆周期的“信用”。从人口角度来看,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5岁以下人口,意味着底层的供需格局发生偏转,且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从技术角度来看,“摩尔定律”的打破或意味着技术进步进入到了混沌区间,脚步停止风险增加。而这些要素的从增长走向衰退,或带来资本要素的扩张停滞,全球经济在陷入增长停滞的过程中,或加剧着存量的博弈,未来趋势性机会或来源于存量环境下安全资产组合的构建:或生成于存量结构的分化(行业层面像能源等传统结构从OPEC转向美国等),或来源于增量结构的改善(目前越南等区域虽无法完整承接别国的产业转移,但部分的产业转移将为该区域提供增量收益)。 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取决于微观实体对于未来扩张展望的信心——企业对于技术、人口、资本回报率等要素识别后作出的长期投资决策。而从理性角度来看,在要素红利回落的过程中,企业的理性决策是守住现金流,抵御漫长的寒冬。但是宏观上看,个体理性的加总却是形成了群体的非理性,带来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失效以及更深刻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微观个体的决策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从全球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全球经济正面临着这一问题的考验。随着2019年标准德债收益率再次跌落至负利率空间,全球负利率资产占比再次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全球收益率为负值的债券名义价值总额再次超过10万亿美元,体现出金融市场追求收益和实际收益空间之间的矛盾,也间接说明了货币政策面临的无效空间——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难以退出(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再也回不到2008年危机之前),以及另一方面无论是常规货币政策抑或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实体周期的平滑效果越来越有限,从市场来看,继续做空波动率资产面临的风险将逐渐抬升。 C硬币的B面:全球流动性的分化 “东方经济学”和“MMT理论”都指出了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货币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但是都有意无意忽视了背后的条件是经济仍维系在趋势向上的环境中。 辜朝明在《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中指出,当家庭和企业因为资产负债表问题或其他问题而被迫做出突然的改变时,或者是行为出现反转时,传统经济学模型就毫无用处。央行通过货币宽松对冲实体经济的债务通缩循环,但是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的下行难以扭转情况下,央行的行为本就在不断压缩政策的有效空间——流动性陷阱。 全球的美元流动性体系重构 过去政策有形之手干预的市场中,形成三个主要宏观变量的分化:金融市场持续繁荣,形成了30年的利率牛市周期;实体经济在全球化末端持续消耗着分工带来的红利增长;由于金融牛市和全球化分化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恶化。桥水基金达利欧指出,目前利率接近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10%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等于剩余90%的人掌握的财富)、阶层固化、政治上民粹主义抬头、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摩擦不断的现状,都和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当前的宏观趋势并未向上。 全球经济和流动性的同向变动加剧周期的恶化。如果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整体,则趋势向下的经济对应的是扩张的逆周期货币。但是在目前的下行状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收紧的美元流动性供给系统。随着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石油美元定价体系之间出现了脱钩,美国贸易项下的石油贸易逆差自2012年开启收缩,预计2019年将达到平衡,不仅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石油美元流动性供给体系面临重新修订,也加重了经济下行过程中的宏观对冲压力,“BW”价差的长期走阔要重点关注。 美国再平衡带来流动性分化 美国通过对外加税、对内减税实行再平衡。除了石油美元项下的流动性收缩,通过贸易规则的重建,继续分化着全球的流动性预期。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结构性无通胀复苏的风险特征,其正通过对外加税实现风险的向外转移——从对美贸易的最大顺差经济来看,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和中国等都是对美贸易最大顺差方。对内美国主要试图通过减税降息的方式缓和内部的结构性压力,2017年年底通过了减税法案,但目前为止美联储利率政策仍维持在相对中性的水平上,另一方面从美联储政策重心从全球转向国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美国货币政策对离岸美元和在岸美元的再平衡。 实施路径上,2017年开始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主要解决的是美元货币区的贸易问题。随着2018年至今多轮的磋商,中美这一美元货币区的流动性因再分配而增加的市场风险正在接近顶点而面临退潮。而随着美元区的贸易再分配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非美元区(主要是欧洲)的贸易问题将重回视野。“欧元-美元”之间贸易流分配问题对于越发显示出疲弱特征的欧洲而言将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我们观察美元和欧元的LIBOR/OIS利差可以发现,在美元相对宽松的阶段,欧元的流动性却呈现出不断紧张的演绎路径,5月的市场关注点在于欧洲议会选举,关注风险发酵带来的欧元兑美元多头入场窗口。 关注中国流动性的重构过程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国内市场需要关注流动性的重构过程。一方面是未来“出口”链条下的美元流动性持续退潮的过程将延续,波动的仅仅是节奏,将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内“房住不炒”政策的驱动下,两个维度的流动性创造可以关注:其一是农村宅基地入市形成的固定资产流动性生产过程带来流动性创造的“存量优化”,其对应的是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改变;其二是市场机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搭建背景下,金融资产抵押品的创设和流通带来的流动性“增量供给”过程,对应的是金融创新驱动的衍生品产品爆发,尽管人口结构已经发生转折,但是对于创新金融工具的需求料快速上升,或成为全球周期末端值得配置的资产。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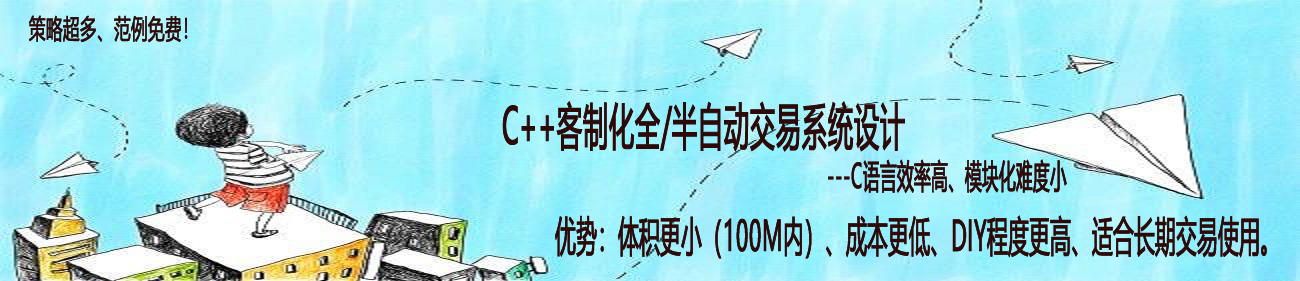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
 2025年最全的Python编程与程序化(量化)教程、视频、源码、课件、资源汇总贴:/thread-152864-1-1.html;
2025年最全的Python编程与程序化(量化)教程、视频、源码、课件、资源汇总贴:/thread-152864-1-1.html;  【1981年-2025年欧美期货、程序化、量化杂志、期货电子书等中文翻译目录汇总!】(注册登录后可看!)
【1981年-2025年欧美期货、程序化、量化杂志、期货电子书等中文翻译目录汇总!】(注册登录后可看!)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