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UID
- 2
- 积分
- 2945117
- 威望
- 1422595 布
- 龙e币
- 1522522 刀
- 在线时间
- 13794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9-12-3
- 最后登录
- 2025-4-24

|
浅析“节能降碳”政策对甲醇行业的影响
小型企业的能耗相对更高,面临的出清风险更大
上周后半段,浙江省印发《浙江省推动碳排放双控工作若干举措》相关文件,该文件共提出13项重点任务,涵盖碳减排及建立健全碳排放双控制度。另外,文件对浙江碳排放权管理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该文件的印发表明“双碳”目标加速落地,也引发了市场对“节能降碳”政策执行力度加强的猜想。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以及《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实施的最后一年,对碳排放和能耗的管控也将更为严格,推动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和高耗能行业的绿色升级工作也是重中之重。受此消息影响,以甲醇为代表的高碳排放和高能耗等品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那么,“节能降碳”政策是否是“能耗双控政策”的2.0版,二者到底有何区别与联系,对甲醇行业有何影响?笔者下面为大家细细分析。
A“能耗双控”政策下甲醇的历史行情演绎
内蒙古是最早因“能耗双控”开始限制甲醇产业企业的地区。2021年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各省份2019年度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考核结果,内蒙古因未完成而被通报批评。此后,内蒙古相继发布《关于开展全区高能耗项目审批建设情况联合调查的预通知》和《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征求意见稿)》等政策文件,开始对当地高能耗企业进行精细化管控,并限制新建高能耗装置。受此影响,2021年2月中下旬开始,内蒙古多家甲醇生产企业(如新能能源、内蒙古荣信、兖矿鄂尔多斯、中煤远兴、世林化工、西北能源、金诚泰等)由原来的超负荷运行变为降负荷运行,并将检修计划提前,涉及产能多达530万吨,这直接导致了西北地区的甲醇开工率在当年3月内从95%左右大幅下降至84%左右,如图1所示。由于内蒙古地区是我国甲醇存量产能规模最大的省份,在“能耗双控”政策发布后,受供给端预期收缩的影响,甲醇2105主力合约从当年2月初的最低2248元/吨稳步上涨至3月初的2682元/吨,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涨幅高达19.31%。2021年8月12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中,内蒙古的“能耗双控”评价达到了“绿色三级预警”,总体进展顺利,内蒙古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取得成效。
然而,在这份“晴雨表”中被亮红灯的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新疆、云南、陕西和江苏等省份则开始下发严格的管控措施,对当地的高能耗企业进行限制,以达到“能耗双控”要求。其中,宁夏、云南和陕西甲醇生产装置相对集中,甲醇产量受影响较大,多地的甲醇装置因“能耗双控”被要求降负或停车。广西和江苏则主要是甲醛、醋酸和甲醇制烯烃等甲醇下游加工企业受到波及,出现拉闸限电被迫停车,其中部分烯烃装置还出现了因甲醇价格大涨而导致深度亏损被逼停的情况,如图2所示。这次“能耗双控”范围扩大对甲醇的短期影响比2021年2月份更加明显,供应端和需求端同时出现了收缩。不过,煤炭价格走高和环保限产问题后,供应端的收缩幅度相对更大,如图3所示。
250213f1.JPG
图1为西北甲醇开工率
甲醇2201主力合约在2021年8月16日跳空高开150多点,而后开启单边上涨模式,不断创出年内新高。后期随着双控政策和能源危机产生共振,在供给端的持续收缩叠加超高成本的支撑下,甲醇期货价格创下4235元/吨的历史最高位。
250213f2.JPG
图2为江苏某甲醇制烯烃装置利润(元/吨)
250213f3.JPG
图3为全国甲醇开工率
2021年我国多个省市实施的“能耗双控”政策,不仅控制了区域内的甲醇等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而且压制了甲醇上下游的产能利用率(对上游开工的影响更为明显),堪比2016年煤炭行业的“供给侧改革2.0版”。从一季度末开始,市场的主导逻辑就由微观的产业基本面转向了偏宏观的政策面。在政策主导下,煤炭等原料价格走高,供应端持续收紧,供需出现大幅错配。“能耗双控”政策在短期内强化了甲醇供应端的收缩力度,甲醇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并发生剧烈波动。一方面,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由于人力成本低,能源价格不高,并且依靠政府支持,企业通常会采取高能耗、高就业的发展模式。在面临“能耗双控”政策的冲击时,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实体企业对政策面的感知、认知相对偏弱,在制定企业发展规划和战略时,往往不会具体地涉及“能耗双控”政策内容,使得当年甲醇产业企业无论是在现货的贸易、生产经营还是在期货的套期保值等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上游企业曾坦言:“往年我们进行市场分析,要看企业利润,要看装置开工,要看下游需求,反而恰恰是不太重视原料端的情况,成本因素只占价格分析、行情预测很小一部分比重。而且从十几年来的情况看,原料确实对甲醇产品构不成太大的影响。但是2021年,以煤为原料的供应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原料恰恰成为行情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上游企业而言,原料煤炭和甲醇价格的宽幅波动影响了其收益,进而影响利润;对下游企业而言,甲醇价格的快速上涨大幅提高了企业的采购成本,进而侵蚀企业的利润,甚至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能耗双控”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产能升级,倒逼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但政策对产业的调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的发布也需要根据市场的导向而改变。2022年开始,我国便开始推进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转变。
B“节能降碳”政策并不是“能耗双控”政策的简单升级
“能耗双控”政策是指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进行控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考核,以达到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和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能耗双控”最早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把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在“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基础之上,进一步要求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明确总量控制目标和分解落实机制。到“十三五”时期,“能耗双控”政策正式开始实施。虽然“能耗双控”政策的实施为遏制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目标缺乏弹性、影响部分重大项目用能保障以及限制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问题,“简单平衡、逐级分解、机械执行”等弊端凸显。2021年以来,“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周期由年度改为季度,形成“季度通报+年度考核”的机制。部分地区为确保完成“能耗双控”目标,采取限产、限电等极端管控措施,虽然短时间内双控数据出现了较大改善,但同样给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产量缩减,市场对商品供需持续错配的预期逐步加强,工业品价格持续上升。此外,最初的“能耗双控”政策是对能源消费进行整体管控,并未区分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早期的“能耗双控”政策存在的问题愈发明显,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2022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强调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2023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至此,在“双碳”背景下,“十四五”规划中的“双控”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碳排放双控”。“碳排放双控”政策以控碳为考核导向,重点约束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而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能耗双控”政策不再限制的原料用能,在“碳排放双控”政策下将被更合理地约束,并可通过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二氧化碳回收、捕集和利用等方式,实现鼓励绿色低碳发展的目的。
“能耗双控”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量,“碳排放双控”目的则是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两者通过行政考核制度设计(激励技术效率提升的强度控制、倒逼消费低碳转型和产业绿色升级的总量控制)以及强制限产类(供给侧主要手段是煤炭去产能、限停电等,消费侧主要是控“两高”、限停产等)和交易类(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为主)手段,都对化石能源消费形成一定制约,也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碳排放量。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二者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减少环境污染。虽然根本目标一致,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一是“能耗双控”政策是对能耗的考核,考核数据为统计量,数据基础较好,考核指标可以从中央层层分解至用能企业;而“碳排放双控”政策直接对“碳”进行控制,考核数据为核算量,数据基础较差,考核对象为省级政府,不可简单的层层分解;二是早期的“能耗双控”政策考核与碳减排贡献不完全匹配,在不区分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难以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碳减排价值,同时抑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碳排放双控”政策更加突出转型的目标导向,对不产生碳排放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没有限制,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与碳减排的统筹协调;三是“能耗双控”政策仅控制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所有能源消费活动,但不控制能源消费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碳排放双控”政策除了控制人类活动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还需要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等非能源活动碳排放。
C“节能降碳”政策对甲醇行业的供给侧影响深远
国务院印发的《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本质上是对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以下简称《指南》)的补充与延续。一方面,“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下降2.5%和3.9%左右,重点领域行业节约标煤5000万吨和减排二氧化碳1.3亿吨”等措辞表明了国内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高耗能行业产能增长受到约束,存量产能位于能效基准水平以下的,2025年年底以前需要技改或清退,这将对高耗能行业的供给侧产生巨大影响,在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同时可以提升中游环节的利润水平。
2022年2月发布的《指南》提及“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煤制甲醇行业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约占25%。到2025年,煤制甲醇行业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我国煤制烯烃行业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约占48%,且全部产能高于基准水平。到2025年,煤制烯烃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比例达到50%”。可以看出,相对于甲醇上游生产而言,甲醇的主力下游(占比超50%)——煤制烯烃产业节能降碳的效果较为显著,暂时不存在产能出清的风险,因此“节能降碳”政策对甲醇行业的供给侧影响更为深远。
由于《指南》将“现代煤化工”细分为了煤制甲醇、煤制烯烃和煤制乙二醇,因此对煤制甲醇装置所涉及的产能需要剥离煤制烯烃/乙二醇一体化装置所对应的甲醇产能。目前我国甲醇产能约有1亿吨/年,煤制甲醇占比在77%,年产能7700万吨左右。其中,一体化装置所涉及的甲醇产能预估在3100万吨,故非一体化煤制甲醇的产能预计在4600万吨左右。按照《指南》要求,国内有25%即1150万吨左右的非一体化煤制甲醇产能在基准水平以下,约占国内甲醇总产能的11%。该部分装置需要在2025年以前通过相关路径降低能耗水平,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可能。
我们认为,建造时间久、设备和技术工艺落后以及用煤标准较高的小型甲醇企业的能耗相对更高,所面临的出清风险也就更大。根据我们的统计,国内20万吨/年以下(不含20万吨/年)的小型甲醇产能约在990万吨(与前述估算量级较为一致),以焦炉气制甲醇和煤联醇装置为主。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焦化行业在环保监查驱动下新旧产能更替的政策开始逐步实施,部分生产工艺落后的中小型焦化产能正在逐步被淘汰和置换。
一般而言,焦化带甲醇的比例大概在100万吨焦化产能带10万吨甲醇产能,通常年产20万吨以下的焦炉气制甲醇装置所对应的焦化厂均属于中小型产能。自2018年以来,不同产能的焦炉开工率开始出现显著分化,大焦炉(产能>200万吨)产能利用率与中小焦炉(产能<200万吨)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差距逐步增加。200万吨以上的大型焦化厂开工率自2017年就一直维持在最高位,而100万吨以下的小型焦化厂开工率自2021年开始大幅滑坡,100万~200万吨的中型焦化厂开工率亦表现出逐年下跌的趋势,这说明我国近年在淘汰落后焦化中小产能上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而甲醇作为焦化企业的副产物,也跟随管控而被动出清。不过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税收和GDP等问题,“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是否会严格执行还有待持续观察,而且本身装置的技改也会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容忍度。
此外,由于企业可以提升开工,因此产能的约束并不是产量下降的充分条件,具体还是需要关注企业实际开工的情况(从2022年《指南》发布开始,甲醇的产量还是在逐年攀升的)。 |
论坛官方微信、群(期货热点、量化探讨、开户与绑定实盘)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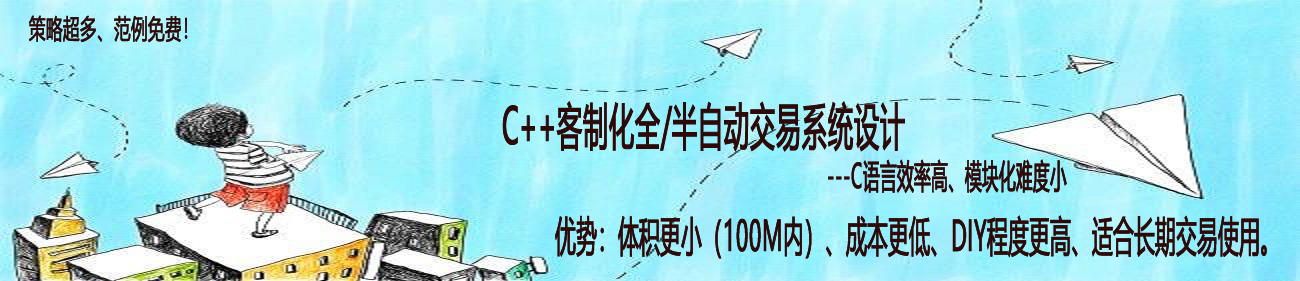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