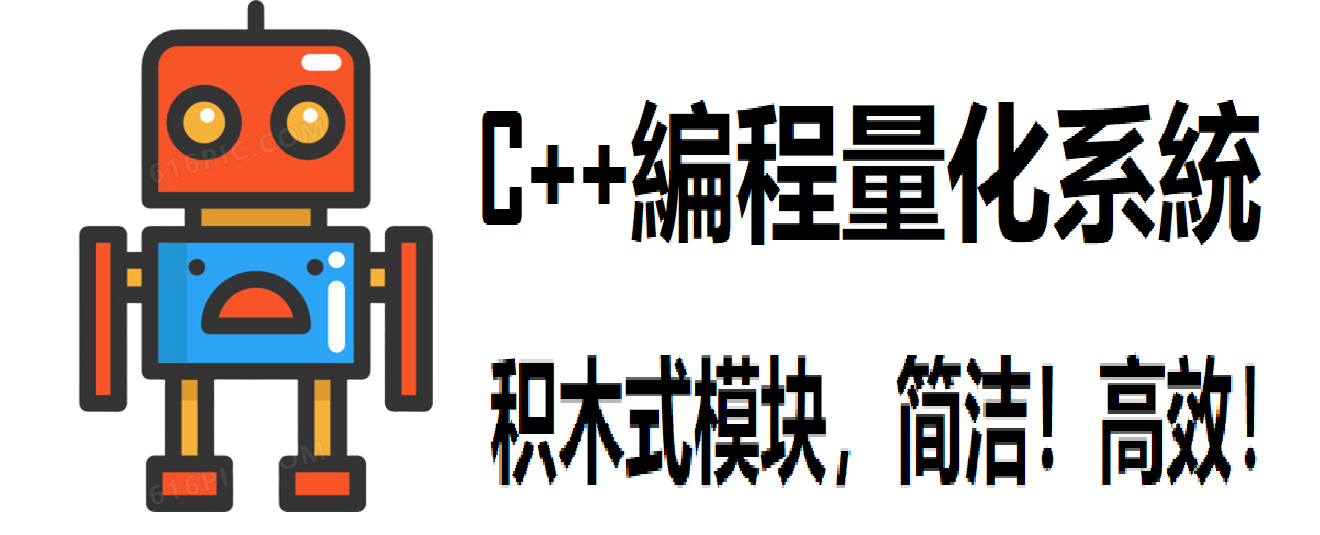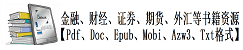|
  
- UID
- 2
- 积分
- 2945767
- 威望
- 1422920 布
- 龙e币
- 1522847 刀
- 在线时间
- 13794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9-12-3
- 最后登录
- 2025-4-26

|
对比国内外关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研究可以看到,尽管国内学者对周期的识别(如主要宏观经济运行变量波动的长度、幅度等)和计量已经有了大量的战略分析,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不仅导致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发现——例如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主要表现为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得不到深入的理论解释,也使得这些研究的关键性结论——利用以市场化改革和减少行政干预为核心的供给面政策来熨平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得不到强大的理论支持,以至于宏观经济运行“过热”或者“过冷”时还是习惯于搬弄总需求政策,而且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这些政策也只能是“行政性”的手段。
为此,本文尝试从中国的禀赋特征——农村劳动力极其富裕这个角度来建立一个理论战略分析框架。显然,考虑到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和转型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这里的理论框架不可能照搬RBC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这样的西方主流理论。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发现,只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还是会显示出其一般的适用性。本文以下将做这样的安排:第二节在对1978年以来总需求的三个构成进行刻画后,提出了战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理论框架;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根据主要宏观经济运行变量的变化,对1954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实证战略分析;最后一节是本文的政策建议。
2、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现象和理论框架
在持续增长的现代宏观经济运行中,衡量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最终指标就是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而研究人均GDP增长率波动的原因又有供给和需求两种角度。由于统计GDP的支出法易于理解,特别是由于长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战略分析、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过程中,GDP的需求即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成为关注的对象。具体说,人们常常不仅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周期性变化看成是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主要表现,而且还将它们直接当作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毋庸置疑,从总需求角度看,GDP确实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但是,要真正理解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还需要从总供给角度来研究GDP——此时,它等于由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决定的生产函数。综合考虑供求两个方面,我们方能理解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三大增长动力变化的原因,从而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乃至宏观经济运行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做出解释。
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供求两种角度可以由下式得到直观的说明:F(A,K,L)=GDP=C+I+(X-M)(1)上式中,左边是技术(A)、资本(K)和劳动(L)等三大增长动力决定的生产函数,右边是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X-M)等三大需求动力决定的总需求。对于这个恒等式,当今两大主流宏观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具有不同的解读方法。以RBC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学派坚持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1)式要从左往右看:在具有自主增长机制的市场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会自发调整,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主要源于供给方发生的技术冲击,所谓的宏观经济运行波动轨迹就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与新古典宏观学派相反,新、旧凯恩斯主义都否定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1)式要从右往左看,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看左边:由于宏观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刚性”或者“黏性”,需求无法自发调整以适应供给的变化,非自愿失业是常见的现象,因此,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源自需求冲击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变化。
考虑到处于转型和发展战略过程中的中国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新古典宏观学派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假说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为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三大总需求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中的表现。
(1)从右往左看(1)式:GDP的需求分解
由于从1978年才开始有通过支付法统计的GDP数据,因此,这里只能战略分析1978~2004年的总需求构成。
凯恩斯认为,随着宏观经济运行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因此,投资在总需求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投资受到“动物精神”的困扰,投资的剧烈波动就成了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主要因素。凯恩斯的这两个结论——消费相对于收入下降、投资周期与GDP周期同步——在中国似乎也成立。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总消费中,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其占GDP的比重都呈现长期下滑的态势,这使得全部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由 1981年的67、5%减少到目前的不到54%。事实上,消费还呈现出反周期的特点:宏观经济运行增长加快,消费占比减少;反之,宏观经济运行增长放缓,消费占比上升。以比重大得多的居民消费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前5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景气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由1989年的近52%大幅度减少至 1994年的不到45%。在宏观经济运行“软着陆”尤其是亚洲战略金融危机之后,居民消费率却一路上升到2000年的48%。在2001年迄今的新一轮宏观经济运行景气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再次直线下降,2004年已经不到42%。这种反周期的消费变化似乎不合逻辑,但是,如果从储蓄的角度来解读,可能就非常自然了:储蓄占比增加,宏观经济运行增长加快;宏观经济运行增长放慢,储蓄占比减少。另外,如果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居民消费率可能是相对平稳的。不过,即使如此,也说明了一个观点:居民的消费决策主要依赖于恒久收入,消费同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并无太大关系。
在消费率长期下降并呈现一定反周期现象的同时,总需求的另外一个部分——投资显然是极度顺周期的。在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增长率由低到高再到低的一波周期中,资本形成率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在1990~2000年间,人均GDP增长率同资本形成率更加体现出高度的同步性。
与消费和投资两大总需求相比,尽管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如同所有的大国宏观经济运行那样,国外需求只是总需求中一个非常次要的组成部分。在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尚呈现出不甚规则的波动。在汇率并轨之后,出口就一直大于进口,即使如此,除了宏观经济运行极度衰退的1997年和1998年曾接近4%以外,其余时间净出口占比基本维持在2%多一点的水平上。
通过以上的经验观察可以发现,在三大总需求中,唯有投资是高度顺周期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投资周期和GDP周期的同步现象,并由此得到相应的宏观宏观经济运行政策含义?显然,没有微观宏观经济运行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基于此的总需求角度是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的。我们以为,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典型事实,并据此提出恰当的宏观宏观经济运行政策建议,必须换个视角来解读(1)式。
(2)从左往右看(1)式:中国的真实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理论
与简单、直观的总需求视角不同,从左往右看(1)式首先要求理解宏观经济运行增长的机制,否则就无法拆解生产函数。在经典的真实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理论文献中,基本的逻辑基础是Lucus和Rapping(1969)提出的假说:技术冲击会引发真实工资和真实利率等变量的变化,这些变量的变化又会导致家庭自发地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最优选择,从而引发就业、产出以及产出主要构成(例如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完全是宏观经济运行当事人规划的帕累托最优轨迹,因此,只存在自愿失业。换言之,失业的增加仅仅是家庭更加偏好闲暇的结果。毋庸置疑,就中国的禀赋特征——大量集中于农村和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而言,这样的逻辑思路和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
为此,针对中国的禀赋特征,李扬和殷剑峰(2005)提出了一个基于劳动力转移的RBC模型,其基本思路是:在额外进行一定的投资后,劳动力可以从当前状态向一种新状态转移,这种转移将显着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乃至工资水平,均衡时人均产出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劳动转移速率完全相等。结合中国的现实,劳动力的当前状态可以理解为农业、农村和低效率的计划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新状态可以理解为非农就业、城市和高效率的市场宏观经济运行体制。这种劳动力在新、旧两种状态下进行选择的机制同正统RBC模型中当事人在劳动和闲暇间进行选择的机制异曲同工。显然,对新状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冲击会导致产出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劳动力转移速率的同时波动。因此,同RBC一样,技术冲击是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产生的主要根源。
不过,既然投资是劳动力转移进而宏观经济运行增长的基础,而劳动力转移又依赖于投资,那么中国投融资体制的不健全必然会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
首先,中国投资体制的改革远远滞后(张汉亚、张欣宁,2005)。即使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看,绝大多数项目依然要核准,而所谓“核准”,其与行政“审批”只是语境上的一点差异。另外,中国的投资体制下投资主体存在着不同于在成熟市场宏观经济运行条件下的特征。在成熟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国家中,投资主体就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并且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态度是:“你投资,我欢迎;你盈利,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你破产,我同情。”在中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不考虑计划宏观经济运行时代单纯以国有宏观经济运行投资为主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后,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以外,还包括国有企业发展战略、集体企业发展战略、三资企业发展战略和个体企业发展战略的投资。在中国投资体制一直延续着计划宏观经济运行时代的审批制度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主体在投资的行业、规模上受到不同的限制,以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会表现出非对称的现象:无论是哪个投资主体的投资,投资的减少都会立刻减少总需求,并导致宏观经济运行景气下滑;但是,由于不同投资主体带动就业进而促进宏观经济运行增长的能力不一样,因此,投资增加对宏观经济运行景气恢复的效力就取决于这些增加的投资来自于哪些投资主体。
其次,中国的融资体制依然处于艰难的改革过程中。尽管近期银行业改革、战略金融市场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拨改贷” 迄今,战略金融体系以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为主体的特征依然没有改变,规模甚小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企业发展战略债券市场)还存在着与投资体制相似的行政审批特征。这种状况不仅使得几乎所有的投资风险战略都集中在脆弱的银行业,而且也使得民营企业发展战略面临的信贷配给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在RBC理论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MM定理成立,因此,企业发展战略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可以不加考虑。但是,当存在融资体系不完美时,融资结构必将影响到投资进而影响到真实宏观经济运行变量的波动。显然,中国战略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行政干预和管制同样会导致投资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且不同投资主体所受到的约束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投融资体制的弊端,李扬和殷剑峰(2005)从风险战略角度抽象地考虑了战略金融体系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由于战略金融体系处理风险战略能力的低下,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因投资约束而在某个临界值停顿下来,这将导致宏观经济运行增长进入收敛状态。在宏观经济运行收敛时产出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都将低于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并且后者还要低于前者。所以,在考虑到体制因素时,宏观经济运行在每个时点都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在劳动力能够由农业、农村和低效率体制向非农业、城市和高效率体制转移的情况下,产出和投资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速;反之,在劳动力转移停顿甚至逆转的情况下,产出和投资的增长会迅速下降,并向一个低水平均衡收敛。
事实上,战略金融体系处理风险战略能力所导致的外生约束完全可以泛化为投融资体制中的各种行政管制。在考虑到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后,不仅技术冲击会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投融资体制的变化——与技术冲击相比,这或许是转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核心因素。不过,无论波动的原因来自于何处,从现象上看,GDP增速、投资增速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始终都应该是高度同步的。
3、计划宏观经济运行时代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1954~1975年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7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战略选择的是“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计划宏观经济运行下的重工业化。1975年邓小平执掌宏观经济运行后,中国开始向现代市场宏观经济运行过渡,而资源禀赋的特征也开始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主导产业结构。这种体制的重大变革意味着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基础性因素,因此,1976年前后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并不具有可比性。换言之,目前许多学者的做法——把20世纪50年代迄今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战略分析是值得怀疑的。在以下对1954~1975年和1976~2004年两个时间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典型事实
计划宏观经济运行时代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具有一个显着的特点:波动幅度极大,不仅增长率的波幅大,而且由于衰退时的增长率常常为负值,因此各种指标的水平值也在大幅度波动。
从人均GDP增速和投资增速看,1954~1975年大致经历了5轮不规则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其中,幅度比较大的周期有两次,两次周期中GDP和投资呈现出高度的同步性:一次是1957~1962年间,人均GDP增速(18、3%)和投资增速(84、5%)均在“大跃进”的1958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人均GDP和投资增速均为负值,谷底都在1961年(人均GDP增速为-26、6%,投资增速为-62、5%)。另一次是从 1963年开始直至1968年,人均GDP和投资增速都在1964年达到顶峰,并在1967年同时达到谷底。除了这两波幅度较大的周期外,在其余的三波周期中,人均GDP和投资增速也是高度同步的。
与GDP和投资的高度同步性相比,就业结构的变化显然另有规律。在“大跃进”中,随着GDP和投资达到高潮,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在非农就业占比方面,1957年还不到20%,1958年却飙升至40%多;在城市就业占比方面,1957年只有13%左右,而1958年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国有单位就业占比方面,1957年是10%左右,1958年达到了近20%;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国有单位就业占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由于农村“大炼钢铁”,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导致该比例从“大跃进”前的50%多剧降至1958年的40%强。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就业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跃进极大地刺激了投资和GDP,但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就业人口结构又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态。
在“大跃进”彻底失败后,就业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迅速上升到70%左右,并在随后的年份里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从1961年国有宏观经济运行确立对非农产业的垄断地位开始,城市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在14年里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农村就业人口向非农业、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基本陷于停顿状态,而这段时间的投资和GDP波动显然仅仅是国有计划宏观经济运行内部的波动,同占比达 70%~80%的绝大多数就业人口并无关系。
总结这段时间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可以发现的三个典型事实是:第一,这一时期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国有计划宏观经济运行内部的波动;第二,投资波动和GDP波动基本同步;第三,如果摒除“大跃进”的影响,投资和GDP的波动同非农就业的变化基本无关。
(2)实证战略分析
上述典型事实已经预示着我们先前描述的中国RBC机制在这段时间并不存在,数据检验证实了这一点:首先,通过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速度(GNA)、投资增长率(GINVEST)和人均GDP增长率(GDPPC)均为平稳变量。这同RBC的标准结论——主要宏观经济运行变量遵循随机游走是完全相左的;其次,既然三变量都是平稳的,在对它们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发现,变量之间均缺乏前因后果的关系;最后,对同年份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时发现,尤其是投资和GDP的相关系数高达90%以上。这些结论不仅说明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自主增长机制并不存在,而且也表明投资本身是作为当期总需求的一部分而非资本积累来推动产出增长的。进一步对投资和GDP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可以发现GDP和投资之间的相互解释程度(R2)高达85%以上,并且人均 GDP增速对投资增速的回归系数几乎就是后者对前者回归系数的倒数——这充分反映了计划宏观经济运行下的整齐划一,但这种高度一致性并不能带动非农就业的增长。
4、走向市场宏观经济运行时代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1976~2004年
从1976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典型事实完全不同于以往,突出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和非农就业周期,另外,还存在着一个时间跨度更大的城市化周期。
(1)典型事实
与1976年前相比,人均GDP增速和投资增速之间的同步性已经明显减弱,这尤其体现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从1976年算起直至2004年,人均 GDP增速经历了三波时间较长的完整周期:第一波在1976~1981年间,历时6年,人均GDP增速在1978年达到峰值(10、2%);第二波在 1982~1989年间,历时8年,人均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峰值13、7%;第三波在1990~2000年间,历时11年,同以往不同的是,人均 GDP增速在1992~1994年连续三年的时间里都维持在11%以上的高平台上运行。
与人均GDP增速相对较长的周期相比,投资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5波短周期,其中,1976~1979年的短周期峰值对应于第一波GDP周期的峰值,1983~1986年的短周期高点也基本上对应于第二波GDP周期的峰值。其余三波短投资周期虽然掀起了GDP的小高潮,但无法扭转GDP周期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仿佛回到了计划宏观经济运行时代,又出现了投资周期和GDP周期完全吻合的现象。不过,这种“复归”显然已经是否定之否定了。在1990~2000年的GDP和投资周期中,投资增速也在1992~1994年维持在高平台上运行。另外,90年代投资还有一波小高潮,即亚洲战略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投资增速上升到13%以上,但是,同20世纪80年代投资尚且能够掀起GDP小高潮相比,1998年的投资扩张显然没有刺激到 GDP。 |
|


 |
|  |
| 










 2025年最全的Python编程与程序化(量化)教程、视频、源码、课件、资源汇总贴:/thread-152864-1-1.html
2025年最全的Python编程与程序化(量化)教程、视频、源码、课件、资源汇总贴:/thread-152864-1-1.html 【1981年-2025年欧美期货、程序化、量化杂志、期货电子书等中文翻译目录汇总!】(注册登录后可看!)
【1981年-2025年欧美期货、程序化、量化杂志、期货电子书等中文翻译目录汇总!】(注册登录后可看!)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