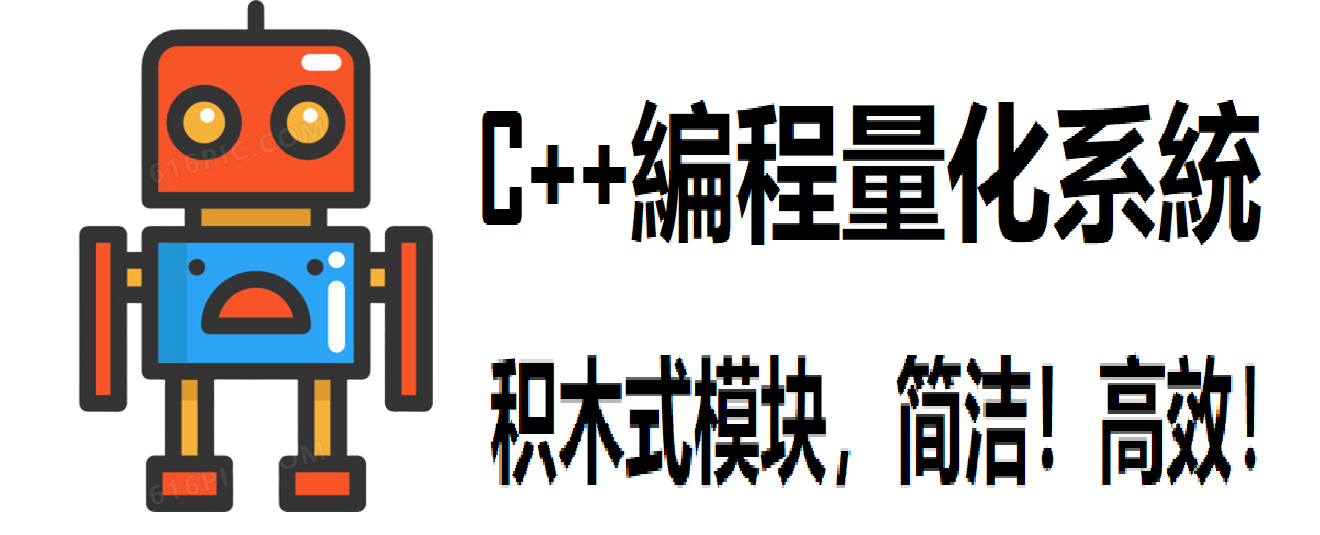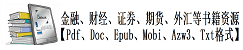水仙花开几案间
寒风瑟瑟,花枝已随雨打风吹去。无花事可问,居室也冷寂。忽一日,花痴太太一手撑伞挡凄雨,一手提篮归家来,笑语惊扰捧读在手的李清照,惊落我念念有词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原来她拎回一株水仙花鳞茎。“快放下你的梧桐,还兼什么细雨,来,搭个手,把花养起。”我垂手在一旁呆呆看着。她利索地取出花盆,蓄上清水,盆底还堆积花花绿绿的雨花石,便给水仙花搭建起新家。我很担心,天气越来越冷,养得活吗?太太懂得我对它的心疼。冷时,搬进屋保暖;有太阳了,还给阳光,享受哺育。不几日,褐黑色根苞中一株株鲜嫩翠白的幼苗浴水而出;隔了一日,根部生出青翠花茎,渐渐舒展开灵性的清绿苗叶;似在不经意间,碧绿的叶茎中间探出一溜花苞;不出两天,一箭花茎伸出水,花蕊已是含苞待放;又过一周左右,借光几个艳阳天,水仙花真的开了——顶端翘然打开一朵朵白色花瓣,吐出金黄色的花蕊……
花不负时,它用洁白的花瓣答谢阳光;花不负人,它用净净的笑脸回报一日一盆清水的辛苦。
每当闲暇之时,我和洁白的花瓣彼此相伴。我在聆听到花开呢喃的声音;它在凝望我舒展的眉头。这个时候,心躁气浮的心境油然而生出超然与清静。
水仙花赐予了我这份心境。何曾想到它是用生命换回——希腊有个神话,一个叫那格索斯的男孩,生下来就有预言,他只要不看见自己的脸就能一直活下去。孩子长大后英俊漂亮,许多姑娘爱上了她,但他对她们冷淡,追求者们生气了,要求众神惩罚傲慢的人。有一次,那格索斯打猎回来,往清泉里看见自己,并爱上了自己的形象,目光离不开自己的脸,直到死在清泉边。就这样,在他死去的地方长出了一株鲜花——水仙花。
喜欢水仙的清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未必知道这个传说。他对水仙爱之如命有另一番理由。他说花里头有他的四条命,水仙居其一。有一年,他先是为了过年东拆西弄,到水仙花开时已不名一文了。家人说:“今年不买花了吧!”他说:“你们要夺去我一条命吗?宁减一年之寿,不减一年之花。”于是,当了妻子的簪环买水仙。此老爱得发狂,也狂得可爱。
其实,水仙也就一草木。诗人、画家,对水仙的情感其实很简单,他和它,可以合作成就诗篇和画卷,用不着支付过多的代价,就能给自己、给世间,经营出吟哦与色彩。
宋代理学家朱熹面对娇娇水仙也会焕发出浪漫诗兴:“隆冬雕百卉,红梅历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风香。”另一首云:“水中仙子来何处,翠袖黄冠白玉英。”与他讲堂上的一本正经相比,懂水仙花的朱熹也更加可爱。
清代扬州名画家汪士慎也酷爱水仙花,他一生画过不知多少水仙,从传世的《水仙图》题句“仙姿疑是洛妃魂,月珮风襟曳浪痕。几度浅描难见取,挥毫应让赵王孙。”便可知其与水仙情谊之重。
鲁迅在《花镜》《广群花谱》里识得水仙花的冰肌玉骨,便笔耕之余,当起了花工。他住在北京时,郑振铎从福建带来水仙花,不轻易接受他人之礼的鲁迅,欣喜地接受了这份馈赠,在植有丁香的院子,养起了水仙。他在这个香溢满院的环境里写成《阿Q正传》。
待水仙静悄悄繁盛之时,我学着文震亨于《长物志》所交代:“冬月宜多植,但其性不耐寒,取极佳者移盆盎,置几案间。”埋着翻书卷,抬着赏花姿。墨香与花香浸渍我的思绪,有凌波仙子相伴,便若入“琵琶阪下是仙乡”的乐天之境。看看书,又看看它;看看它,又摸摸水底的小石子。将自己与水仙花,与小石摆在一起,似是互为知己。恰似爱画水仙的吴昌硕诗言:“水仙洁成癖,石头牢不朽。落落岁寒侣,参我即三友。谪仙何耐烦,邀月更携酒。”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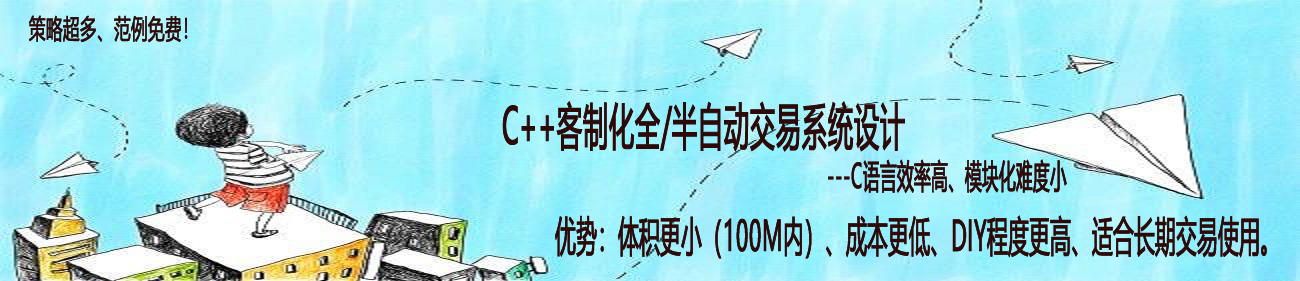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