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清日月明
清明时节桃花水。经历了一冬的萧瑟,水很寂寞。待到春来,田地肥润,众鸟皆啼,万物蓬发,水也显示出迫不及待来。春夜的一场雨,把山河灌醉,把田间地头的沟沟渠渠也撑得绿水横溢。
在田间地头走,汩汩的水流声萦绕耳畔。哪怕舞台是小小一条沟渠,春水也状若奔流,水流之急,让人宛若置身于长江边。那气势,恰如牛犊初生,亦似雏鸟展翅。若田地间稍有落差,春水便形成一截短瀑布,哗哗声不绝于耳,有“飞流直下三千尽”之势。
白居易有诗云“春来江水绿如蓝”。春水此时的绿与别时不同,那是绿得逼人心魄的绿,是带些浑浊的绿。此时的春水,来势汹汹地证明着自己,砂泥俱带。那锋芒是韬光养晦了一个冬季之后的喷发,难免有飞出牢笼的张扬,有年少气盛的猖狂。
然而,水到底是智慧的。它不允许自己一直张扬下去、猖狂下去、浑浊下去。待到清明时节,仲春已过,暮春启程,水也慢慢变得恬淡。
春水盈盈,不再绿如蓝,而是绿得干净,绿得澄澈,绿得谦卑。
又一场春雨来,伴随呼啸的闪电、炸耳的雷声。待天明,世间绿意盎然,春水潺潺。那水,一改初春时的恣意昂扬,变得温柔如风。它稳稳地穿过沟渠,绕过丰茂的水草,擦过灌木丛林,低低地走,静静地流。清明清明,智慧如水,怎能不除浊见清,除伪见明?
清明时节,绿遍山野,鸟鸣声把所有林子都装满。阳光在肩上背上跳跃,是一首灵动的歌,是一幅明丽的画。
此时的阳光,在我看来,大抵是一年中最好的。酷暑的阳光过于炙热,烤得人坐立难安,那是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霸道,是让人觉得密不透风的压抑。纵然那时,云朵绮丽,碧空万里,却也让酷热的阳光折煞了美感。深秋的阳光与清明时节最接近,都是那么柔软,那么轻盈,然而悲伤等在前头,叫人不忍步步往前走。那时,秋光很好,天高水浅,也还有稀少的蝉在叫,然而也意味着马上就要掉入冬的冷窖。独爱清明时期的阳光——藏着花香,带着昨夜雨水的余味,还暗含着很多希望。
在种瓜点豆的时节,人们还穿着春天的衣服,然而心里已经装着夏天的洒脱,挥着锄头,领着耕牛,顶着一身阳光,就像戴着一身花环。
在很多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顶着阳光在奔跑,跑过闪着粼粼波光的池塘,跑过浑身披绿的山坡,跑过已经冒出很多野草的田塍,多想顶着温暖又和煦的阳光,穿过四季和无常。
年少时常看外婆卤笋。清明前后,竹笋前赴后继地冒出来,鲜笋吃不完,就晒一些笋干,或用头一年腌制咸菜的卤水煮一锅卤笋以备日后慢慢食用。
乡下人舍不得花正而八经的时间卤笋,就把晚上的时间挪进来。待卤香四溢,外公早已把一张小方桌搬至门外的场子上,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白瓷碗,夹几筷子鲜卤笋,拎一瓶烧酒,奔往门外。
月光像孔雀开屏,突然间亮起来,又或许我之前根本不曾注意到它。外公就着月光,呷一口酒,往嘴里送一块笋。四周突然很安静,是王籍诗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静。后来看过林清玄先生的妙文《温一壶月光下酒》,我以为温一壶清明时节的月光是最好。那时的月光,明亮而不聒噪,清冽而不忧伤,一切都刚刚好。
墙脚已有蚯蚓低吟,远处池塘边或有蛙鸣徐徐而来,空中时不时有昆虫扇翅而过,矮墙边的凤仙花已长出长长的苗,似要马上开出花来,一切像处在混沌之中,然而又井然有序,一切似乎都很暧昧,然而又泾渭分明。此时的月光,是一壶纯厚的酒,口感柔顺,又不上头;是一朵荆棘花,长得清丽,又不魅惑。
那一束清明时节的月光,是大地的一副清丽的妆。
清明值暮春,草木葳蕤,鸟鸣满涧。慢下来,低下来,给大地、给万物,一个深深的贴面礼。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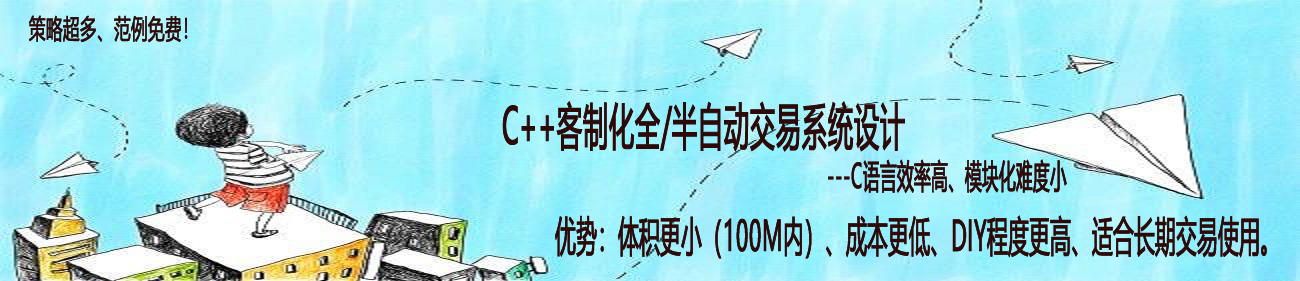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