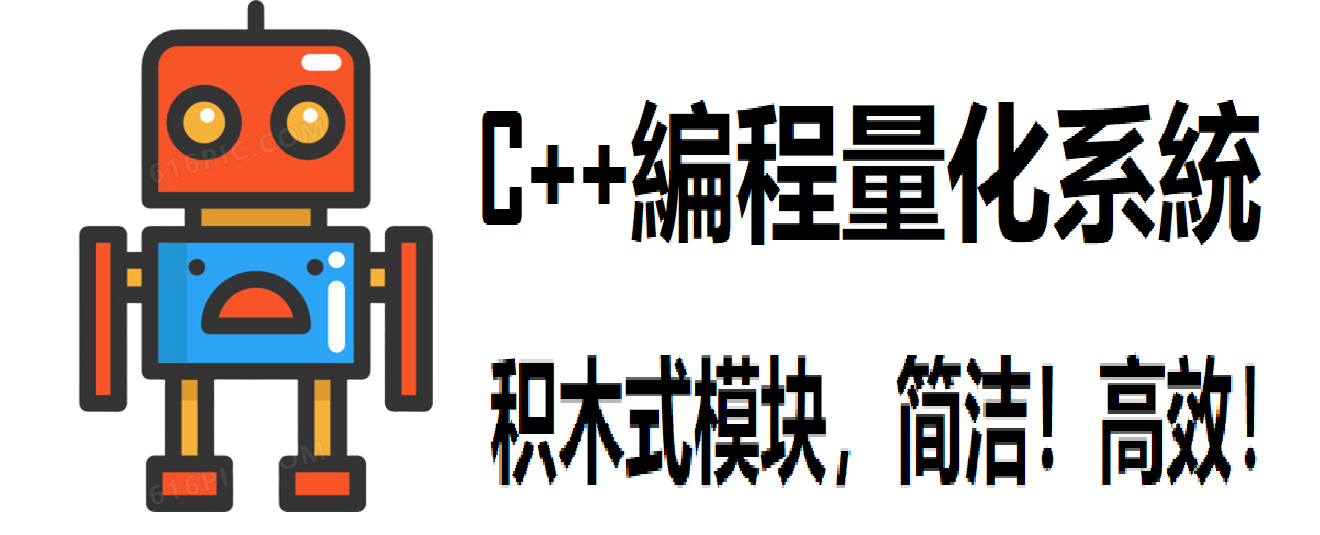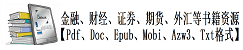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 ——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 “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 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 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 ——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主权,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 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 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 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 F.A. 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 der komplementaren 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 der 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 (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 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 der 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 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代理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 Menger,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1883; Die Irrthu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okonomie, 1884; Grundzuge einer Classific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Conrad's Jahrbuh fur Nationalokonomie und Statistik, N.F., vol. xix, 1889; Sax, Das Wesen und die Aufgabe der Nationalokonomie, 1884; Philippovich, Ueber Aufgabe und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86; Bohm-Bawerk, Grund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1886, pp. 480, et seq.; review of Brentano's Classische Nationalokonomie in the Gottinger Gelehrten Anzeigen, 1-6, 1889; review of Schmoller's Litteraturgeschichte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translated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1, no. 2, October 1890.
2. Entwickelung der Go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3.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2nd, ed., 1879.
4.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hschafslehre, 1871.
5. Elements d'Economie Politique Pure, 1874.
6. "Philosophy of value" in the New Englander, July, 1881. Professor Clark was not then familiar, as he tells me, with the works of Jevons and Menger.
7.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38 and 49;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1889, pp. 46 et seq.
8. As for example in Germany, the highest authority on the theory of price, Hermann; cf.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516, 527.
9.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of price; Menger, Grundsatze de Volkswirtschaftslehre, p. 142, et seq., Bohm-Bawerk, Grun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Part II,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p. 477 et seq., and on the point touched upon in the text, especially, p. 516;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37 et seq.; Sax, Grundlegung der theoretischen Staatswirtschaft, 1887, pp. 276 et seq., Zucherkandl, ZurTheorie des Preises, 1889. I will not lo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er to the excellent account given by Dr James
Bonar, some years ago, of the Austrial economists and their views of value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1888.
10. Der Naturliche Werth, p. 170
11.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 of cost and value; Menger, Grundsatze, pp. 123 et seq.; Weiser, Ue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1884, pp. 139 et seq.;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164 et seq.; Bohm-Bawerk,
Grundsuge, pp. 61 et seq., 534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1889, pp. 189 et seq., 234 et seq.
12. Menger, Grundstze, pp. 138 et seq. Bohm-Bawerk, Grundzuge, Part I, pp. 56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pp. 178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67 et seq.
13.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 201.
14.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isinstheorien, 188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preface by W. Smart, 1890] II.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es, 1889; differing from the older teaching of Menger's Grundsatze, pp. 143 et seq.
15.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assim, and pp. 450-452.
16. Mataja, Der Unternehmergewinn, 1884; Gross,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1884.
17. Menger, Grundsatze, pp. 133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te Werth, pp. 112 et seq.;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p. 380 et seq.
18. Robert Meyer, Die Principien der gerechten Besteuerung, 1884; Sax, Grundlegung, 1887;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209 et seq.
19. Mataja, Das Recht des Schadenersatzes, 1888; Seidler, "Die Geldstrafe vom volks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politischen Gesichtspunkt"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1890.
20. Menger, Grundsatze, pp. 8 et seq.
21. Bohm-Bawerk, Rechte und Verhaltnisse vom Standpunkt der volkwirtschaftlichen Guterichre, 1881, pp. 57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pp. 361 et seq.
22. By Sax, for example, Die Verkehrsmittel in Volks und Staatswirtschaft, 1878-79; Philippovich, Die Bank von England, 1885; Der badische Staatshaushalt, 1889.
页:
[1]

 QQ: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