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子
邓析(前545-前501), 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老子和孔子基本同时,是战国名家的鼻祖,著名的讼师。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谈到: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反对将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邓析生前著作基本已失,目前仅存《无厚》《转辞》两篇。
[color=#000]邓析是第一个用法律作武器,开辟律师诉讼的先河。其思想“不法先王,不是礼仪”。私作“竹刑”,聚众讲法,为民众诉讼,因而得罪当权者而获刑。郑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color] 《邓析子》01章 无厚
天於人无厚也,君於民无厚也,父於子无厚也,兄於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於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於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於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於弟无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工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失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安得不危!
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诚听能闻於无声,视能见於无形,计能规於未兆,虑能防於未然,斯无他也。不以耳听,则通於无声矣!不以目视,则照於无形矣!不以心计,则达於无兆矣!不以知虑,则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动者,用不失则利。故明君审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务,智不可以从他,求诸己之谓也。
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所美观其所终,所恶计其所穷。喜不以赏,怒不以罚,可谓治世。
夫负重者患涂远,据贵者忧民离。负重涂远者,身疲而无功;在上离民者,虽劳而不治。故智者量涂而后负,明君视民而出政。
猎罴虎者,不於外圂,钓鲸鲵者,不於清池。何则?圂非罴虎之窟也,池非鲸鲵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陈之不束麾,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
夫游而不见敬,不恭也;居而不见爱,不仁也;言而不见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无媒也;谋而不见喜,无理也;计而不见从;遗道也。因势而发誉,则行等而名殊;人齐而得时,则力敌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势之在外推。
辩说、非所听也;虚言者,非所应也;无益之辞,非所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
死生自命,富贵自时。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贫贱者,不知时也。故临难不惧,知天命也;贫穷无慑,达时序也。
凶饥之岁,父死於室,子死於户,而不相怨者,无所顾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张罗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悦者,颜不能不笑;责疲者以举千钧;责兀者以及走兔;驱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槛。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而索领。
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忧也。
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故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达道者,无知之道也,无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无有而足,守虚责实,而万事毕。忠言於不忠,义生於不义。音而不收、谓之放;言出而不督、谓之闇。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无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无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处非所处,则失;道非其道不道,则谄。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言虚如受实,万事毕。
夫言荣不若辱,非诚辞也。得不若失,非实谈也。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为一矣。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知浅故也。君子并物而错之,兼涂而用之,五味未尝而辩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无方之道不从,面从之义不行,治乱之法不用。惔然宽裕,荡然简易,略而无失,精详入纤微也。
夫舟浮於水,车转於陆,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不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载焉。故有知则惑,有心则崄,有目则眩。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为之也。
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闇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明君知此,则去就之分定矣。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搤睕、手据鞭朴、而后为治欤。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与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故远而亲者,志相应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无违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远而相思者,合其谋也。故明君择人,不可不审;士之进趣,亦不可不详。 《邓析子》02章 转辞
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久惑於此。今转之,在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在己若扶之与携,谢之与议。故之与古,诺之与已,相去千里也。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於博;与博者言,依於辩;与辩者言,依於安;与贵言者,依於势;与富者言,依於豪;与贫者言,依於利;与勇者言,依於敢;与愚者言,依於说。此言之术也。
不困,在早图,不穷,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口;非所宣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争,勿争,以避其声。一声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故恶言不出口,苟语不留耳,此谓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则不任也,慧则不从也,仁则不亲也,勇则不近也,信则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谓之神。怒出於怒,为出於不为。视於无有,则得其所见,听於无声,则得其所闻。故无形者有形之本,无声者有声之母。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仁义而穷之。何以知其然?彼窃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耶?故逐於大盗,揭诸侯,此重利盗跖而不可禁者,乃圣人之罪也。
欲之与恶,善之与恶,四者变之失。恭之与俭,敬之与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忧而无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为信,言有善而不为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於无法。立君而争贤,是贤与君争,其乱也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心不欲躁,虑不欲浅。心躁、则精神滑,虑浅、则百事倾。
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上古之乐、质而不悲;当今之乐,邪而为淫。上古之民,质而敦朴;今世之民,诈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世有墨劓,不以为耻,斯民所以乱多治少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此四君子者,圣人也,而犹若此之勤。至於栗陆氏杀东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诛龙逢,纣刳比干,四主者乱君。故其疾贤若仇,是以贤愚之相较,若百丈之谿与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与重山之颠。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亲而疏之,疏而亲之。故畏俭则福生,骄奢则祸起。圣人逍遥,一世罕匹。万物之形,寂然无鞭朴之罚,莫然无叱吒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视昭昭,知冥冥,推未运,睹未然。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此之谓也。
君人者不能自专而好任下,则智日困而数日穷。迫於下则不能申,行随於国则不能持。知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无以与下交矣。故喜而使赏,不必当功;怒而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诛赏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杀君不绝。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发言欲胜,举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长;不以其拙,疾人之工。言有善者,明而赏之;言有非者,显而罚之。塞邪枉之路,荡淫辞之端。臣下闭口,左右结舌,可谓明君。为善者君与之赏,为恶者君与之罚。因其所以来而报之,循其所以进而答之。圣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今之为君,无尧舜之才,而慕尧舜之治,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觉於昭明之术。是以虚慕欲治之名,无益乱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祸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终如始也。富必给贫,壮必给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贵无以高人,聪明无以笼人,资给无以先人,刚勇无以胜人。能履行此,可以为天下君。
夫谋莫难於必听,事莫难於必成,成必合於数,听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烁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独行之术也。
明君立法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此之谓君曰乱君,国曰亡国。
智者察於是非,故善恶有别;明者审於去就,故进退无类。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审去就,斯谓虚妄。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於不为也。 《邓析子》邓析的命定之路
春秋战国,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
子产,郑国的大夫,在一次国家动乱之后被推上了郑国执政的位置。子产一改过去统治阶级所认为的“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观点,认为法律的公开能更好地确保它的执行。公元前536年,子产将新制定的刑法的条文铸在一个青铜鼎上,史称“铸刑书”。这也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成文法,比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大约早一个世纪。
改革者在改革的前期必定是孤独的,因为改革所带来的正面效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现。而利益受损者、保守者和批评者却可以在第一时间以充分的理由反对变革。这一点从郑国普通民众对于子产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改革初期,郑国普通民众对于改革十分不满,当时的民谣中充斥着对子产新政的嘲讽和攻击,有些歌谣甚至唱到:如果有谁想去杀子产为国除害的话,可别忘了通知我一声。
面对着社会各阶层的强大压力,子产进行变革时不得不向既得利益者阶层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刑书中,子产部分保留了贵族阶层的特权,也正是这种政治妥协使子产没有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成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英雄。到了改革后期,受益者越来越多,改革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民谣中支持和歌颂子产的声音多了起来。
如果将子产称为执政的法律家的话,那么,邓析就是一名“在野法律人”或“民间法律人”了。与子产改革必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甚至不得不屈从于强势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在野者和时政批评者,邓析更多的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诉求出发,这就决定了同是法学家的两位哲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成文法的实施和诉讼制度的施行,使得法律服务的必要性应时而生,邓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打官司为生计的法律人了。除了帮人家打官司(诉讼代理)外,他还帮助别人出主意解决纠纷(非讼业务)。此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法学教育家,聚众讲学,招收门生,向人们讲解、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
也许是邓析并不在乎金钱,也可能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作为中国律师业开山祖师的邓析先生,其收入比起当今的一些大律师可以说是寒碜。对来请教和求助的人,大的案件收一件外衣,小的案件则收一件短裤。当时拿着衣服和短裤前来求助或求学的人络绎不绝,也不知邓析是否开一家成衣店来处理这些律师费和学杂费。
邓析是中国法治史上第一代具有现代律师职业特征的法律人,可以说是中国律师业的鼻祖。他所开设的学校,采用的是案例教学法,通过对经典判例的分析并让学生在模拟审判中思考,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这种教学方式,在一百多年后的希腊城邦,由于一位哲人的采用,故被称为苏格拉底教学法,在今天外国法学院教育中,仍被广泛采用。
邓析还经常批评子产先生的法律改革并不彻底,给贵族阶层太多的特权。他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法律。他逐条批评子产所制刑书的不足,并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制定了一部新的刑书。由于当时的青铜可是一种贵重金属,于是邓析将这部刑书刻在竹简上,后人称之为“竹刑”。
或许,居庙堂之高的郑国执政者子产从内心中也是认同甚至佩服同是法律人的邓析的一些真知灼见的。没有史料证明子产和邓析经常交往,但子产对于“乡校事件”的处理方法,也证明在没有现代传媒和代议制度的时代,邓析的批评意见还是有可能通过线报传到子产的耳朵中,作为决策的参考。
子产执政时,郑国的一些知识阶层经常聚集在乡校中,议论子产的施政方针。当然,其中的批评意见居多。子产的手下认为乡校议政的无政府思潮极大地损害了执政者的威严,在讨论中直呼国家领导人的名讳更是大逆不道,建议子产派出军队捣毁乡校。
但子产不同意,他认为乡校是自己的老师,“其所善者,吾则从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不仅不关闭乡校,反而经常派人混入其中,将所有的议论记录下来分析。而当时,邓析是乡校的常客,批评意见也最为尖锐且正中掌权者的命门。因此,即使子产没有机会和邓析秉烛夜谈、煮酒纵论天下,他那批评的声音通过细作的密报还是能进入子产耳中的。
作为一名无官无爵的自由知识分子,又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邓析完全可以率性而为,针砭时弊。他不屑于先王礼义的传统价值理念,而主张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明断是非,主张废除贵族们的特权。
不同的是,子产是个法学家的同时,更是个精明的政治家━━真正的法律人是不会因为时势的不同而放弃或隐瞒自己的观点的,而政治家则不同。
我们不能苛责子产改革的局限性。在社会急剧变革,社会各阶层分化重组、利益博弈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执政者的子产的任何一个重大举措的出台,都如同在高空中走钢丝且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或退路,稍一不慎,《春秋》中又将多了一个不幸者。
主流社会对于邓析所从事的职业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邓析所做的,无非逞“口舌之利,操两可之说,设无究之词”而已。特别是儒家,他们认为:辩士和讼师的存在,利用逻辑推理的名辩方法,投机取巧,使得民风变得刁顽,人心不古。追求通过道德教化从而达到天下无讼大治状态的儒家,是十分痛恨邓析们的存在的。
大儒荀子在他的著作中认为:邓析替人代为诉讼的方式无非是“好治怪说,玩琦辞。其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即使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也不喜欢邓析的存在的。在邓析被杀后的数百年,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变法。同样也是持法家思想的秦国相吕不韦在召集其门客所著的《吕氏春秋》中,提到邓析时仍然持批判的态度,认为邓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并认为邓析的好讼与好辩是郑国政局不稳的祸根。
事实上,邓析并没有错。律师必须忠实于委托人。他考虑任何问题,都必须站在委托人的立场,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在这过程中,合理地利用或规避法律的漏洞,也是无可指责的。
驷颛执政时,郑国正陷入政治危机之中。新的执政需要一个政治上的替罪羊。公元前501年,邓析被杀,罪名是未经允许私自制定法律《竹刑》。但值得讽刺的是,在邓析被杀之后,执政者却决定采用《竹刑》作为国家的制定法。
于是邓析终于死了。他的死,似乎象征着一种职业在中国法治史上的昙花一现。与希腊和古罗马不一样的是,辩护士在中国的传统法庭上终究没能成为一种骄傲的吸引优秀人才参加的职业。更多拥有聪明才智和口才的人如苏秦、张仪之类,更渴望的是运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合纵连横,货与帝王家,谋繁华富贵于朝夕。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邓析,静静地躺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诉说着一段如烟如梦的往事。
同中国的法治本土资源中,律师这一职业角色从此缺位。直到清朝末年的沈家本奉诏修律,这一名词才第一次被引入。此时,距离邓析被杀已经过了2400年。 《邓析子》千古诡辩第一人
在以法治国的今天,律师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过,律师是一个“舶来词”,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一称谓,古人将从事律师职业的人称为讼师。
在中国数千年的司法史中,讼师始于何时?追根溯源,据史料记载,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叫邓析的政治家,他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并帮人打官司,因而,邓析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讼师的鼻祖。
邓析不但是古代第一位有据可查的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他还创造了数项第一:第一个编修了私家刑书;第一个进行普法宣传;第一个使用“大字报”引导老百姓参政议政,成为中国最早的民主斗士!
中国最早的斗士
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数风流人物”,历朝历代没有多过这个时期的。邓析与孔子都处于这一时期,然而,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孔圣人”是妇孺皆知,至今仍备受推崇,很多人却只把邓析定位于讼师,其实,邓析曾是一位引起社会轰动的、颇有反叛色彩的响当当的人物。
邓析的一生,连续做了两件轰动天下的大事:一是私造竹刑,使法律不再由封建贵族独自掌握,而是走向了普通大众;二是助讼讲学,鼓励老百姓参政议政。
2005年1月28日,谈到邓析,原新郑市党史办公室主任郑中智先生介绍说,邓析生于公元前545年,是春秋晚期的新郑人。邓析在青少年时代就“好为智巧”,头脑灵活,很有学问。成年后邓析做了郑国的大夫,是一个基层的低级小吏。
在邓析生活的时代,法律曾经完全是由贵族们独自掌握的“专利”,对平民百姓一直是秘而不宣的。法律是贵族们手中的“橡皮泥”,贵族们愚弄老百姓是常有的事情。
邓析是一位敢于向时代和权威挑战的勇士。郑中智先生说,子产当上郑国执政大臣后,以周朝的礼仪作为司法准据,“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称为鼎刑。邓析成为郑国大夫后,反对以旧礼作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要求摒弃旧制,进行刑法改革,主张“事断于法”。邓析“欲改郑所著刑制,不受君命而私造竹刑”,由于深受子产铸鼎刑的影响,邓析吸收了很多人的意见,私自拟定了一部新的法律条文,并把这些法律条文刻在竹简上,在民间传播,进行法治宣传,让人们学习和掌握法律,在守法的同时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受到群众的欢迎。人们称邓析私自拟定的法律为“竹刑”。
竹刑比鼎刑造价便宜,易于传播,使得贵族和平民都能看到法律条文,提高大众的法律意识,也保护了平民的利益。邓析制定“竹刑”之举,揭开了法律的神秘面纱,促进了法律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使法律终于走向了大众。
郑中智先生说,邓析是个很有民主意识的人,他积极提倡平民百姓参政议政,引导群众用贴匿名帖的方法揭发当权贵族和大夫们的过失,议论国家的政事。匿名帖就是在文革中曾经泛滥成灾的“大字报”。如此一来,那些贵族们便害怕老百姓揭发他们的罪恶,对邓析很反感,便向继子产之后的郑国执政大臣驷颛告了邓析一状,说邓析用匿名帖煸动平民百姓闹事,要造反。于是,驷颛下令老百姓不允许贴匿名帖。
不允许贴匿名帖的禁令并没有使邓析退缩,他又教老百姓改变方式,用“致书”的方式来评议时政,就是把贴匿名帖改为寄匿名信,将议政的内容相互传递,甚至把举报揭发一些当权者犯罪的材料寄到执政大臣驷颛那里。驷颛又下令不准老百姓传寄匿名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邓析又想出了“倚书”的办法,就是把评议时政的信夹寄在包裹里的其它物品中,继续相互传递,使匿名信一直难以禁止。
在两千多年前的专制时代,邓析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私制竹刑,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法制意识,而引导平民百姓参政议政,不但需要杰出的智慧,更需要不怕掉脑袋的勇气。邓析以其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在民间传播着民主法制思想,因此,有学者把邓析誉为中国最早的民主斗士!
千古诡辩第一人
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学说的成立,无不经历了辩论的检验和洗礼,经过辩论而站得住脚的学说才能够深入人心。“理越辩越明白”,辩论推动了人类思想的发展。
辩论这种艺术,始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以研究辩论术著称的论辩家,被称为“名家”。邓析是中国古代名家的先驱,以擅长辩论著称,他常常以论辩的形式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其辩论之术无人能敌。
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赵宪立介绍说,史书记载邓析常常“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说邓析同时肯定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性质,提出两个逻辑上对立的判断,分别论证这两个判断的正确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论证,他都有无穷的对答之辞。邓析做了大夫之后,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询问农夫的生产情况。当时,农夫们还是用瓦罐背水浇地,看到他们笨拙的劳作方式,邓析很体恤农夫的辛劳。于是,邓析就和农夫们一起反复研究试验,利用杠杆的作用,发明了一种提水工具———桔槔,就是在田里的水渠边立一根木桩,把一根比较长的木杠横架在直立的木桩上,木杠的一端用绳子系上水桶,另一端用绳子绑块石头作为平衡的力量,由人工操作,把低处的水提到地面上浇灌农作物。
应当说,邓析是一位了不起的革新家。赵宪立先生介绍说,桔槔是当时生产条件下最先进的农具,原来农夫抱瓮一天仅能浇1畦地,用桔槔提水一天能浇100畦地。邓析将桔槔提水的技术推广到了卫国等地,桔槔这种提水工具一直被人们沿用了2000多年,新郑人称其为“窝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一些因循守旧的人们宥于成见,竟然不肯使用桔槔。面对这种不求进取、甘愿落后的社会现实,邓析于是开辩论之风,他认为辩论可以明是非、分清浊,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邓析善于辩说,常常“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而可与不可日变”,这样的辩论也给人留下了诡辩的印象。先秦吕不韦编著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记载了邓析的一个典型的诡辩故事,郑中智先生讲了这个故事:
新郑境内有条著名的洧水。有一年发大水,郑国有个富人渡河时不慎失足落入洧水中淹死了,其尸体被一个穷人打捞上来。富人的家属听说后想用钱赎回尸体埋葬,打捞尸体的穷人了解到死者家里很有钱,觉得奇货可居,就漫天要价,想趁机捞一把。富人不想出那么多钱,双方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僵了。
情急之下,富人的家人便向邓析请教解决的办法,邓析说:你们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因为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向他买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穷人自然会降价的!富人的家人觉得邓析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过了几天不见富人家来买尸体,那个穷人坐不住了,也来找邓析出主意。邓析对那个穷人说: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不要降低,因为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穷人一听有理,也不着急了。
这就是邓析有名的“两可之说”,被后人称为“名师之辩”!千百年来,邓析创造的这一诡辩的经典辩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邓析被誉为“千古诡辩第一人”。
这场尸体讼案充分显示了邓析的口才,邓析的辩说技巧由此可见一斑。同一个事实,邓析却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每个结论听起来都言之有理,这种诡辩的手法确实很厉害,邓析诡辩的目的在于希望当事人相持一段时间后,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平衡点。邓析的诡辩看似荒谬,但有人由此感悟出了个中奥妙———某些时候,人类若不模棱两可,世界将会剑拔弩张到何种地步?
古代讼师的开山鼻祖
在中国古代,打官司首先要向官府递交诉状,老百姓能识文断字者并不多,于是,专门替别人写讼状,为当事人打官司出谋划策的讼师就应运而生了。中国古代的讼师,是现代律师的萌芽。赵宪立先生介绍说,邓析不仅法律知识渊博,精通诉讼之法,并且能言善辩,是一个在法律和辩论方面二者兼备的专家。而春秋时期出现了诉讼代理制度,诉讼当事人不必亲自到官府打官司,其下属或子弟等可代理进行诉讼,这种社会环境为邓析提供了用武之地。
邓析乐于为民讲理,他常常以自己的博学和雄辩,帮人书写诉状,帮助老百姓打官司,是中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讼师。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讼师的开山鼻祖当为邓析。
时间长了,老百姓之间如果发生了什么纠纷,都去找邓析请教解决的办法,当然少不了要送给他一些礼物作为酬金。帮人打官司,邓析约定按照案件的大小收费,大案件收取一件外衣,小案件收取一条短裤,类似今天的收费律师。当时,拿着外衣、短裤前来找邓析咨询诉讼者络绎不绝。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代理的官司总是获胜,每场官司下来,“郑国大乱,民口欢哗”。邓析不但亲自帮助别人打官司,而且还大力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教别人学习诉讼。赵宪立先生说,春秋末期已出现私人创办的学校———私学,邓析也创办了一所私学,他聚众讲学,除了讲授自己的著作“竹刑”,还专门教人怎么打官司,教授给别人讼辩的技巧。据《左传》记载,邓析创办私学,“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可见其私学之兴盛。
邓析还鼓励平民百姓告状揭发贵族和大夫们的罪行,这样一来,打官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使得一些大夫和贵族不敢再胡作非为。邓析这种知识型官僚亲自作讼师投身于诉讼者,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邓析之后的各朝统治者大都禁止讼师劝人兴讼、教人为讼,视讼师代理诉讼为非法并对此严厉查处,以保证皇权的统治和老百姓的顺从。但邓析的身后却跟上来一批又一批追随者,讼师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和政治制度边缘上矛盾地存在了数千年。
法家思想的祭品
在邓析的倡导下,当时的郑国兴起了一股诉讼的浪潮,却触犯了当权贵族们的利益,致使当权贵族们对邓析怀恨在心。当这种矛盾日益激烈时,作为法家先驱者的邓析便惨遭杀身之祸。郑中智先生说,久而久之,有一些当权贵族和大夫就跑到执政大臣驷颛那里说邓析的坏话,认为他只是“治怪说,玩奇辞”,把他称为“作伪之民”,驷颛视邓析为扰乱民心的祸首。公元前501年,为了维护当权贵族的利益,驷颛将邓析杀害,并展尸示众。
然而,由于邓析的《竹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要,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还是在郑国得到大力推行。邓析的“竹刑”竟然为他的政敌所用,足以证明邓析对法律的研究是相当精到的。当时驷颛为杀邓析找的理由是邓析“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但杀了邓析,却又要用人家的“竹刑”,这不能不说是件具有讽刺意义的怪事儿。《左传》曾引用孔子的话,说驷颛不应该对邓析“用其道”而“不恤其人”。
有学者指出,邓析被“杀其人而用其刑”的结局昭示出了后世法家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像邓
析一样,法家人物凭借其切合时代的思想主张及个人才干赢得了君主们的赏识,但遗憾的是大都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邓析如此,韩非也是如此,先秦法家人物身首异处的个人悲剧与其思想主张流传后世的胜利形成了鲜明而深刻的矛盾对比。然而,法家人物的法治主张多为后世所继承,他们取得了思想上的最后胜利,所以受到后人的崇拜!
邓析虽然倒下了,但在中国法制史上,邓析无疑是一座永恒的丰碑,因为他是中国从封建专制时代走向民主法制时代的一颗闪光的铺路石!时至今日,邓析仍然受到后人的崇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就特意被命名为“邓析堂”,邓析堂大门口立有一块碑,碑文对邓析作了高度概括性的介绍———
邓析:春秋末郑国法学家。他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是为《竹刑》,被国家采用。……他是我国第一个私家法典草案的起草人,第一位“律师”,第一位私人法律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因讲求法律逻辑而牺牲的人。 《邓析子》邓析与传统精神资源
邓析之死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传统面临进步时的杀伐之气不可避免。逮后,经由商鞅,闭死了法治(而非法制)的大门;经由李斯,闭死了自由思考的大门;经由董仲舒,闭死了精神多元发展的大门。这样,传统剩下的有价值的东西也就很有限了。
面对这样的传统资源及其自闭命运,新儒家们能有何作为呢?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主持制定了国家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众。他公布刑书的形式是把所有的法律条文一一铸在鼎上,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比较早的“成文法”,更是比较早公开公布的“成文法” (《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的说法。据考,“象以典刑”的意思就是:在器物上刻写法律规定以及刑罚手段。似乎中国很早就有了公布成文法的事例。但《尚书·舜典》的记载似乎不足凭信。)。在中国的法学发展史上,此事意义重大。
“刑鼎”颁布后,国人“争之以刑书”,形成了法律自动普及的乐观局面。法律公开,普通百姓就可以援引法律条文维护自己利益,一般来说,一向口含天宪的统治者对此是绝难接受的。法律、法令、法规,就是规则,而习惯于极权统治的领袖们是不喜欢按规则办事的。就这个意义而言,郑国的法制改革值得尊敬。据史料记载,子产公布成文法,曾经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反对,甚至国际间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远在晋国的大夫叔向就专门写信给子产,表示谴责(有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晋国,23年后,也开始效法郑国,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出来)。子产这一举措,由于它的珍稀性,在中国,可以用伟大来评价。
公开公布的成文法,官方与民间都要根据它来打官司,这就有了讨论的余地。于是,解释,开始了泛滥。各色人等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刑法条文,国人对此有了热烈的辩论。辩论中,邓析的《竹刑》应运而生。
邓析,又称邓析子,是名学的创始人,此人精通逻辑,郑国“刑书”颁布后,邓析子开始研究“刑书”,并以自己的博学和雄辩,钻郑国法律的空子,帮郑国的百姓打官司,邓析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律师。不仅如此,邓析还开始招收生徒讲学,自由地传授他所理解的法律知识,邓析的策略就是利用郑国的刑书合法斗争。估计他可能总是游走于郑国刑法的边缘,所以总能从利益对峙中倾向于平民一边。按照《吕氏春秋·离谓》的说法,邓析总是代表民间成为官司的获胜者,每场官司下来,“郑国大乱,民口欢譁”。我倾向于认为,郑国此时出现的法典公开与公众参与事件,与后来的周共和行政事件,是两千年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民主性质的最重要的经典性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周王朝中期的“国人”对于争取民权具有可喜可贺的自觉性,推翻周厉王的暴虐统治,实行“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光荣革命”——清世逊位或可当之——或者与法兰西民众的多次革命有相似之处。章太炎在晚清,曾经保有激进民主倾向,他是最早剪发的革命党人之一,剪发后,并作《解辫发》一文,文中不屑使用清廷纪年,就使用公元前八四一年“共和行政”为中国纪年,径曰著文当年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 。)
《竹刑》可能是在子产的成文法基础上作出的更为详尽的司法解释(?),且便于操作,也许还更为公平。根据《左传·定公七年》的记录:“(子然)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一段记录看,《竹刑》很可能是比郑国刑法更为完善的法律文本。
但是郑国官方像中国历代官方一样,没有能力因势利导,从此打造出一片法制天地来,而是对来自民间的“异己”力量心怀恐惧。历史经验证明:当官方开始恐惧的的时候,杀戮也便开始了。公元前501年,邓析,终于被郑国杀害。(出于我对子产先生的尊重,有必要指出,杀害邓析的不是子产,而是子然——子产此时已经死了。)
后来的日子,成文法是不是还可以公布,让民间也让官方“依法办事”呢?从此似乎没有。官方,特别是执政的官方首领,最喜欢的是“临事议制”、“法自朕出”;子产、邓析云云,于是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绝唱。
说邓析“私造刑书”,杀了;又用人家邓析的“刑书”,这事儿构成了中国历史独特的政治风景。 与后来的“商秧死而商君之法行”是一脉相承的丑陋事件。这个,且不去说了。想说的是,假如郑国或轴心时代的中国其他统治者们,能够具备梭伦、伯里克利那样的胸怀,能够将民权看得重于君权,能够天才地把握进步文明的趋势,因势利导;假如那个时代的人民能够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能够团结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并产生富有政治智慧的民运领袖;假如共同体之间的交互性能够生成最初的理性,就象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那样,中国的历史面貌和政治命运必将改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非理性(或曰:实践理性)合力,断送了轴心时代路径延展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郑国的被统治者也有责任,“郑国大乱,民口欢譁”,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证据。尽管邓析的斗争策略有公开性、合法性、非暴力的演进性质,但“大乱”云云,也应有民众情绪失控,导致非理性泛滥,危及威权统治的因素)。毕竟,民主,需要理性的烛照。
当代新儒家,比较温和的一个流派,在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或民主运动的精神资源时,邓析,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若干精英,或者不能忽视。传统资源不仅仅在儒家一家,在法家,在名家,也并不少见。但是这些资源,是否有其历史的承续性,是否可以经由创造性的解释转化为新的精神资源,在现成的“异邦”资源可以“拿来”的时侯,有无必要“旧瓶装新酒”,等等,尽管我有乐观其成的倾向,但还是愿意保留一点儿谨慎的怀疑。
铸了“刑书”、“刑鼎”向国人明白展示,确是中国法制史上最值得圈点的动人事例。大约与子产、邓析同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跃动着现代司法精神的法治管理理论思想,比如《法经》、《管子》所论及的“事断于法”,“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罚必当”,等等。应当说,这类思想确实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法制思想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与“刑书”“刑鼎”一起,具有了类似《汉穆拉比法典》成文法的性质。但也必须看到,这类法制思想的进步性是有限的。譬如前述传为李悝所著的《法经》就有一项严重的反人道规定:议论国家法令罪。所定刑法极重,处死刑,抄没家产,妻子为奴。国家的法令是不准议论的!这正是钳制民口的高压兼愚民政策。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子产公布的郑国刑法和邓析的《竹刑》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根据中国现存的法律文献推断,很可能是“刑法”与“民法”的杂糅。中国古代,一向是“礼”与“法”不分,“刑法”与“民法”不分的,封建社会的法典,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有关田土、钱债、户籍、婚姻等法律规定或规范,统收在各朝律、例之中。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起草于1911年即宣统三年,称为《大清民律(草案)》,但还远不完善。抵1929-1930年间,中国陆续公布了《民法总则》各编,才算正式有了民法。
但中国的法律著作却并不罕见。自汉代以后,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或“刑罚志”)又有“十通”、“会典”、“会要”之类,再加上历代文人笔记、各类野史杂著,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如《云梦秦简》、《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后人据此钩稽,编为法制史资料汇编,往往颇具规模,如1934年孙绍祖撰成的《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收集历来法学著作572种,1957年大陆编成《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收集历来法学著作932部,1976年台湾纂成的《中国法制史书目》,收集历来法学著作2473部。这么多的“法学著作”,其中的法典类不在少数,成文法也不在少数,但由于中华法系“临事议制”的特点,历来为中国百姓所了解、通晓的法典,寥寥无几。法典,从来就不是中国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对于中国百姓而言,成文法也往往行同虚设。这些东西,与现代法治其实是没有多少有意味的关联性质的。
“刑书”、“刑鼎”的颁布肯定不是统治者的恩赐,但也更不是“人民流血斗争的结果”,事实上,那是老牌贵族在动荡时代渐被新兴的“布衣卿相” 打破法权法统垄断的结果。毕竟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或者也可以解释为,这是轴心时代先民为了更合理地生存,经由国家机器表现出来的利益均衡运动的结果。当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一场利益均衡运动没有持续多久,到了商鞅的时代划上了句号。商鞅没有继承中国法权体系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却将极权专制的法权体系推向了时代的巅峰,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国民“争之以刑书”的大好局面。从此,中国与法治绝缘——这是中国两千年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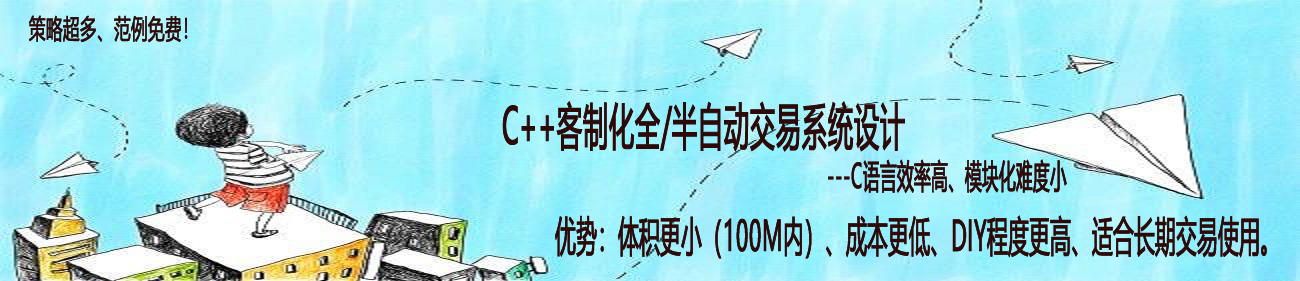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