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危机分析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问题【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10~15
【作 者】赵磊
【作者简介】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邮编:610074
【内容提要】当下学界流行的方**分类尚不足以把握主流经济学方**的本质。从“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来看,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是“经济人假设”内在的硬伤。20世纪中期以来,长期支配西方经济学方**的“唯心教条”遇到了来自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挑战。如果说以往的挑战还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撑,那么基于实证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挑战就不能再被视为无稽之谈了。于是我们看到,在放宽“假定”的不断退让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渐遭到侵蚀。承认这种“侵蚀”,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的演变趋势。
【关 键 词】西方经济学/唯心和唯物/方**/经济人假设/行为经济学
【正 文】
用“唯心”和”唯物”来为经济学的方**分类,当今恐怕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目前有关经济学方**的分类早就突破了“唯心”和“唯物”的理论框架。然而,分类的意义毕竟不只是方**的重构,更不是方**名称的堆积和数量的增加,而是在于对不同方**的根本性质的比较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并没有过时,依然是科学识别和把握西方经济学方**本质有效工具。基于此,本文以“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为依据,考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的危机及其发展趋势。
一、内在的硬伤:用“心理”解释“心理”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四个“结构前提”和一个“经济人假设”。这四个结构前提是:给定的“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和“制度安排”。而“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则是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这种从个人本性出发的分析理路,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即学术界通常归纳的所谓“个人主义方**”。其实,“个人主义方**”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方**的特征之一,用“个人主义方**”来概括西方经济学方**只是从分析元素上的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经济学方**的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四个结构前提”把技术、偏好、资源和制度锁定在孤立的、静止的状态下,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经济人假设”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方**。因此我认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才是西方经济学方**的本质所在。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的行为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决定的。用心理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也是它的学术传统。比如凯恩斯关于“决定有效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论,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经济人假设”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虽然符合人们当下的经验直觉,却存在致命的内在硬伤:它无法说明“人的心理倾向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人性而不是“那种”人性?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有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心理活动的,如贝克尔(Garybecket)在《社会经济学》中,通过“社会资本”概念将社会规范和他人价值观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引入经济分析框架,确认了社会因素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注: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学》,《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但是,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有意回避,主流经济学泰然自若地固守在”唯心”的阵地上。
对于私有制社会而言,“经济人假设”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并不抽象,它不过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这个“并不抽象”的假设使“经济人”的解释力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时空范围,“经济人假设”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把“物质动机”视为经济人“利已”行为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不明白,“物质动机”不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动机”成反比,与“非物质动机”成正比(注:马斯洛等:《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这个道理在今天已经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动机”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动机”(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自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头,我们就清楚了。
其实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观察视角出发就已经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心理基础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由此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唯心”的方**,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寻找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动因。在“唯心”的方**的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拒绝历史地解读人类的心理活动,把“理性”和“利己”视为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纪以前,“经济人假设”就曾遭到了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和制度主义(凡勃仑)的抨击。(注:参见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虽然这些抨击相当尖锐,但由于其依据主要来自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故难以对西方经济学的“唯心”视角构成真正的威胁。
然而,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只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追问”是无法回避的。20世纪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的“唯心教条”开始遇到了无情的反叛。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来看,有四个学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两种理性主义: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人类主观意识设计的产物;二是进化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自发”进化的产物。哈耶克从“进化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强烈地质疑了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发现:“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注:转引:张宇等:《马克思是建构主义者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是建构主义的典范。哈耶克把理性主义区分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其本意不是要清算主流经济学的方**,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建构主义”加以“批判”。有趣的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不偏不倚地正砸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心方**的要害处。他将“理性”区分为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不仅说明他意识到了这种区分(“自发”和“人为”)是方**的本质要害所在,而且表明了在西方经济学方**中出现的微妙变化:否认建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对西方经济学“唯心教条”方**的怀疑(尽管这是不自觉的)。我认为,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经济学者高明之所在。
第二个是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西蒙认为,“经济人假设”中的“无限理性”一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在现实中,人的理性会受到以下条件的制约:(1)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2)信息的不完全性;(3)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人们的认知能力和“理性”程度就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只能是“有限”的。因此,人们的行为选择标准不会遵循“完全理性”给出的“最优决策”,而是遵循“有限理性”给出的“满意决策”。(注:参: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自从“有限理性”提出以来。不仅“经济人假设”的解释力从此缩小了,而且西蒙强调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对主观心理活动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对主流经济学“唯心教条”的公然反叛。
第三个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的“嵌人理论”。格兰诺维特把“经济人”称为“低度社会化人”。由于“低度社会化人”把人的行为看作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格兰诺维特从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出发,就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富有“唯物”色彩的“嵌入理论”。认为人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个人似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是“嵌人”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注:汪和建:《“经济生活的新经济学”:一个批判性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6期。
Granovetter,M.Economic of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J].American JournalofSociology,1985,(91).)他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第二,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换言之,他认为经济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选择,很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遗留,仅靠理性选择不能充分解释经济行为,而经济学在剔除“非经济动机”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注: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批判》,《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嵌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入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击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的“唯心主义”要害。
第四个是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其实是经济学中“成本”(耗费)概念的引伸,但交易费用并不是单纯的物的“成本耕费”,而是人与人打交道(经济关系)的“成本耗费”。交易费用通常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交易费用”,把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化,从而否定了“黑板经济学”对“经济人”那种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从交易费用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方面,对促进主流经济学“回归现实”也做出了努力,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没有说清制度的起源但承认了制度的历史性、可变性,不再把制度看作是“给定的”,而是看作内生于经济过程之中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
三、卡尼曼和史密斯的挑战
说到“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有两个人物不得不提及:一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另一个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史密斯。前者是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后者是“实验经济学之父”。由于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两人共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类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实验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实验的方法和技术考察人的心理倾向,从而为经济学提供了检验、分析行为选择的有效工具。二者的研究结果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实实在在的不利证据。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发现了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的反常现象。
(一)理性反常。
按照“经济人假设”,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并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为人也能通过概率来判断比较各种可能方案的预期效用。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在不少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根据“成本与收益”而是根据“其他的依据”进行决策,因而效用难以实现“最大化”,“经济人”甚至并不追求“最大化”。这些“其他的依据”是:(1)现实世界存在着行为人不能克服的困难,限制了对“最大化”的追求,(2)行为人的心理认知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出现了偏离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结果。例如,1985年卡尼曼等人做了一个著名的“银行出纳员实验”,实验主体被告之:林达主攻哲学,她深深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并参加反核示***威运动。实验主体应据此判断林达是:a.女银行出纳员;b.女银行出纳员和活跃的女权运动者。结果有近90%的实验主体选择了b。该例说明,行为决策中出现的偏见往往是外界因素“启示”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判断时常常过于看重显著、难忘的证据)和“框架效应”(即信息的不同表达方式会引导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是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常见现象(注:参见魏建:《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常现象”》,《经济科学》2001年第6期;湛志伟:《坎内曼与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制约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复杂性。
(二)偏好反常。
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其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因而是不变的。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人们的偏好并不是连续的、稳定的,而是可变的。1990年,特维尔斯基和塞勒做了如下实验:第一步,要求实验主体在两个期望值相同的赌博中进行选择,H赌博以较高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小的价值(比如以8/9的概率赢得4美元),L赌博以较低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大的价值(比如以1/9的概率赢得,10美元)。结果有71%的人选择了H赌博。第二步,要求上面的实验主体给两个赌博定价,让他们标出愿意出售两个赌博的各自最低价。结果有67%的人对L赌博给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发现,在实验的前期人们偏好H赌博,而在后期却偏好L赌博,这种被称之为“偏好颠倒”(preferencereversal)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偏好颠倒”的实验对于我们确认人类心理活动的历史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三)利己反常。
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人”的追求目标是自我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反例与此不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人到餐馆吃饭付小费。如果说付小费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人们一般是在用完餐后才付;如果是为了将来得到更好的服务,可是多数人在偶然光顾的餐馆里也付小费,不付小费并不会受到起诉,而付小费却直接减少了行为者的自我利益(金钱)。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利己反常”?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原因除了对社会规范的尊崇以外,更在于人们对“自我利益”以外的价值(如公平)的强调。比如,在一个“团体交换”的实验中,每个实验主体得到了同样数目的货币,要求他们对一个“团体交换”的公共项目投资(每个人的投资额是保密的),并告诉他们,投资完成后所有人(不论是否投资)都将平均分配投资收益。按“经济人假设”判断,投资不会发生。但实验结果是:实验主体平均投资了初始货币额的40-60%;重复实验的结果也表明,投资比例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虽然在下降,但不会降为零;实验中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重新开始效应”,即每当宣布实验重新进行多少次时,下降的投资水平又回升到40-60%。该实验说明,尽管“搭便车”的行为会压抑人们的投资热情,但愿意为公共事业尽力的心理也是人之常情。
尽管行为经济学的根基依然是“心理分析”,但它多少已经触及了心理活动背后的因素(社会环境)。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一致性和非历史性),而且在于寻求心理活动“唯物”基础的努力(心理活动的唯物性和历史性),并取得了初步成绩。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言:“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和在中国的实践都指向同一个演化方向——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人的影响。”(注: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学》,《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事实上,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理性也好,非理性也罢,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本原都是“唯物”的,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而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的行为都可以在现实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得到科学的解释。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强劲攻势下,我国经济学界似乎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渐行渐远。然而,看来“马克思幽灵”有着极强的生命力,100多年以后,如果说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傲慢可以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指手划脚,那么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再次确认了人类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历史性,无意之间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证明。这不仅是主流经济学难以接受的,恐怕也是行为经济学始末预料到的结果。
四、结语
概括以上分析,可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
(1)西方主流经济学方**的危机,并不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反常”行为。这一点,即使是来自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学者也难以断然否认了。如果西方经济学不放弃方**的“唯心”视角,“经济人假设”对发展着的实践的解释力就会越来越弱,直至最终被颠覆。我国学者汪丁丁曾敏锐地看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注: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然而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汪丁丁却并未深究。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个“基础”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方**的“唯心”视角。
(2)由于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根源于其方**上的“唯心”视角,因而他们也就无法理解:经济人的“反常”行为恰恰是人性并非永恒不变的一个写照和注脚——今天的“反常”在明天可能就是“理性”,今天的“理性”在明天可能就是“反常”,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为了给这些“反常”行为一个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好不断放宽“假定”。然而,放宽“假定”固然能暂时与现实保持一致,却与“唯心”的观察视角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于是我们看到,在放宽“假定”的不断退让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渐遭到侵蚀。承认这种“侵蚀”,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的演变趋势。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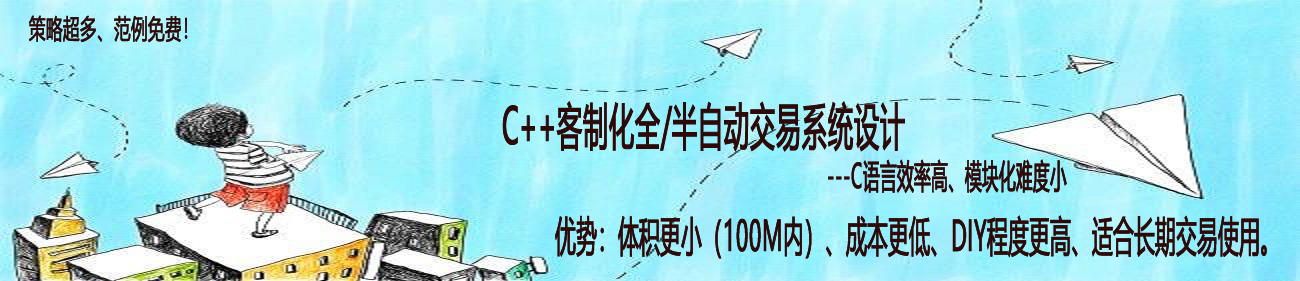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QQ:
QQ: